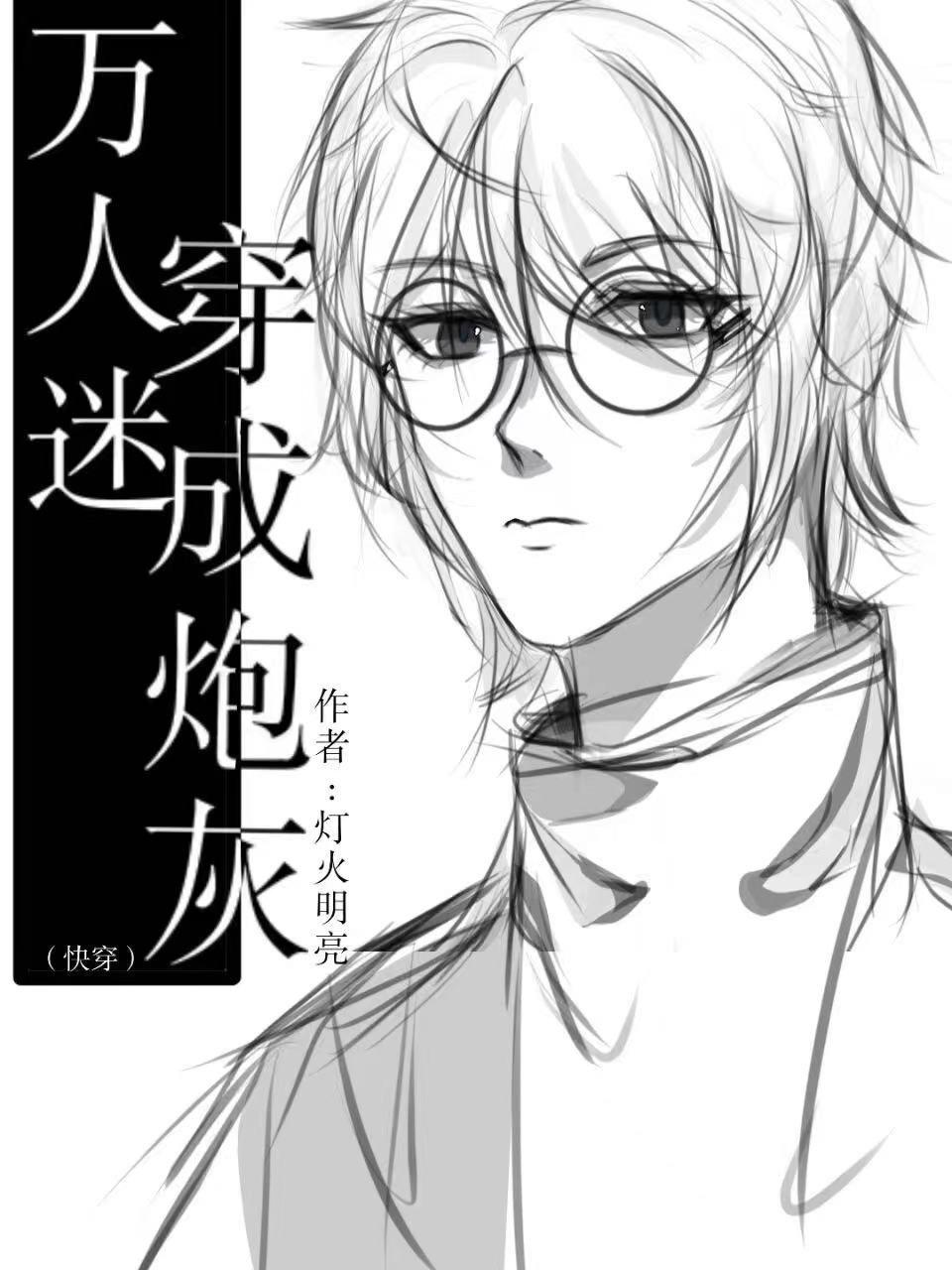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夺棠青山远黛全文免费阅读 > 59 跪下 跪你你当我是疯了吗(第1页)
59 跪下 跪你你当我是疯了吗(第1页)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百花争妍。近来,顾锦棠和绿醅每日都会往坊市间去看铺子,倒也初步择定了几间,只等明日再去瞧瞧便定下其中一间。
奔波一天归家后,顾锦棠下厨做了两菜一汤,与绿醅相对而坐用着晚膳,忽听外头传来王婶的声音,道是有话要与她说。
顾锦棠便叫她稍稍等上些时候,她用两口饭就过来,王婶闻言,让她慢慢吃就是,自己在厢房里等着她,不必急在这一时。
那厢房原是给上门拜访需要过夜的亲友住的,平日里几乎都是空着,不过王婶是个手脚勤快的,室内倒也打理得干净齐整。
用完晚膳后,绿醅负责收拾桌子清洗碗筷,顾锦棠出门去厢房寻找王婶。
王婶见她进来,浅笑着让她往自己身边坐下,亲自替她斟上一盏茶递到她手边,柔着声问她:“三娘可信佛?”
顾锦棠摇摇头。
“那可是信道?”王婶面上笑意微不可查地深了一些,满脸期待地看着她。
顾锦棠犹豫片刻后,又摇了头。
这下子,王婶愈发高兴,激动地拉起顾锦棠的手滔滔不绝地说起燃灯教的好处来,又道教首推算出她现下住着的宅子里有个家中行三的女郎乃是天上仙子下凡,只要入了燃灯教,即刻就可成为圣女。
她家中除开她以外统共就三个女郎,她的女儿和蕊娘都是独女,说的不可就是她眼前的这位三娘么。
为着让她入教,难为王婶竟能想出这样一套说辞来。顾锦棠只觉得她真是被那燃灯教洗了脑了,思忖良久后方开口认真道:“婶子,咱们在一处住了数月,彼此之间多少是有些情义的,我早就发觉你入了那燃灯教,原是不想多言的,可你今日这番话着实叫我无法再装聋做哑,需得推心置腹地同你说道一番:那燃灯教并非朝廷认可的,这会子朝廷虽未做出什么反应来,可难保他日不会生出变故,婶子还是早早地抽身出来,信佛、道也好,什么都不信也罢,总之这燃灯教,绝非如婶子你现下看到的那般简单。”
王婶观她神情严肃,非但不肯入教,反而劝她退教,当即也不好再多言,怕她会愈加抵触这件事,只得模棱两可地道声她会考虑仔细看看,悻悻离了厢房。
是夜,顾锦棠竟是有些睡不着,自她与绿醅来到江城以后,她是吃得香得喝香睡得也香,就连宋霆越那厮都不曾来能力扰过她,又哪里失过眠。
身侧的绿醅被她时不时翻来覆去地动作扰到,少不得问上一句,顾锦棠犹豫要不要将王婶入了那燃灯教昏了头的事告诉绿醅,思量再三终是只道了句明日过去将铺子盘下,后日便叫驴车过来搬东西住过去。
绿醅不明白她为何这般急,可她向来是个有主意的,做何事都有她自己的理由,到底没有多言,选择全心全意地相信她,听她的话。
次日一早,二人一道出门,王婶站在廊下看着她们走出去,交代刘小娘子几句话,换上一身干净的素服不知往何处去了。
顾锦棠和绿醅回来的时候,王婶先她们一步,这会子已经在给刘小娘子做糕点了,看上去同往日里那个勤劳能干的王婶并无甚么不同。
绿醅站在厨房外头和她打招呼,又叫刘小娘子过来,给她送了个舶来的小玩意。
刘小娘子欢天喜地地谢过她,拿回屋自个儿乐呵呵地顽去了。
在江城的这段时间太过快意,绿醅都快要忘了在王府里的那段日子了,一心一意只想着怎么和顾锦棠一起经营好她们的茶馆。
一整个下午,顾锦棠都在收拾东西,待收拾地差不多了,绿醅端着两碗面进来,笑盈盈叫顾锦棠尝尝她的手艺,眼神里满满的都是期待。
待听到顾锦棠用上一口夸赞她后,她才满心欢喜地也坐下来吃面。
其实要开一间茶馆并不容易,从桌椅到茶盏再到每一道茶和糕点的名称,皆是要费心择定的,绿醅着实体会到了凡事都要亲力亲为的小商人的不易。
春日不必日日都沐浴,因明日还要早起,顾锦棠洗漱一番往床上躺了,绿醅坐在灯下拿面脂抹完脸,起身欲要吹灯往床榻安歇,忽的浑身乏力腿下一软,失去意识直直往地上倒了下去。
床上的顾锦棠本就乏了,睡得越发香甜。
待她清醒之际,入眼的是一间陌生的石室,没有窗子,也看不见外面,甚至不能知晓这会子是白天还是黑夜。
这一切都太过于诡异,不免让她以为自己是在做梦,抬手掐了自己的手臂一把,疼痛觉十分清晰。
这不是梦。顾锦棠瞬间清醒过来,起身下榻去推那道石门,任她怎么用力,那石门并未挪动分毫。
直至外头的人听到声响,不多时,石门从外面打开,一个戴着面具的女郎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两个同样戴着面具的女郎。
这般不敢以真实面目示人的做派,不禁让她想到了声势浩大的燃灯教。
“你们是燃灯教的人?”即便心里有了答案,顾锦棠还是问了出来。
为首的白衣女郎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我不是什么世家大族的娘子,亦不是那等腰缠万贯的富贾,你们将我捉来此处意欲何为?与我同住的女郎你们又将她如何了?”
想起绿醅,顾锦棠顾不得害怕,抬眸死死盯着那白衣女郎,忽然觉得她身上透出来的气息很是熟悉。
“三娘且安心,只要你乖乖做了我教的圣女,蕊娘自会好好的。”
竟是薛九娘。
顾锦棠错愕地睁大眼睛,一脸的不敢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