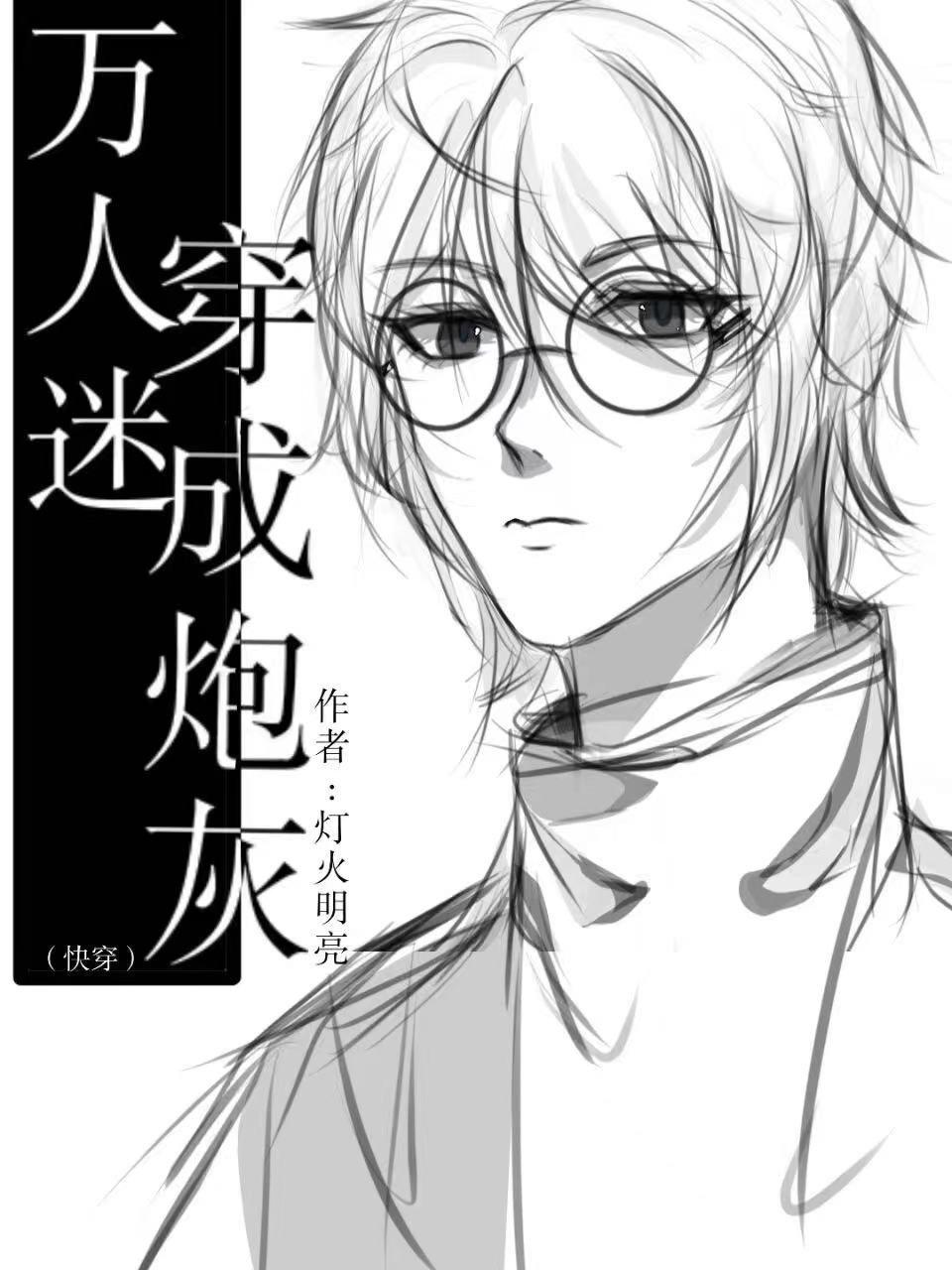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穿到渣A折磨女主前免费 > 2第二章(第1页)
2第二章(第1页)
宋姣缩在床铺上不住的发抖。
许今朝已经出去有一会儿了,她起初还在外面制造出一些动静,现在却没有任何声息。
她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alpha为何突然改变想法,不打算对她用强了。但宋姣仍然怕得浑身哆嗦,小口小口喘着气,拼命积蓄体力。
宋姣躺了好久,可能有二十分钟,可能有半个小时,又或者其实只是五分钟,因为她已经完全丧失了对时间流逝速度的准确感知。
她像一只被车撞了、奄奄一息躺着的流浪猫,窝在那里动弹不得。
不是宋姣不想起来,她发了疯一样的想把自己藏起来,想躲得许今朝远远地。
但宋姣做不到,alpha充满恶意的信息素扭绞了她的精神,只艰难的拢起手脚、把自己蜷回婴儿在母亲子宫中的样子就已经让宋姣耗掉了全部力气。
她刚退了低烧,沐浴后换上长袖的纽扣睡裙,把身体从上到下谨慎遮掩。
可现在被alpha粗暴拉扯开,棉质的裙摆狼狈堆皱在腰胯处,宋姣却无力哪怕伸手去扯一扯,为自己保留起码的体面。
许今朝的气味还残留在空气里,易感期失控的alpha信息素辛辣且充满了攻击性,宋姣每呼吸到一点,就抖动得更厉害。
她怕极了,她真的怕了。
她怎么会天真到以为能保全自身呢,她怎么会天真到以为凭借意志可以抵抗本能呢……该怎么办,该怎么办。
宋姣的自尊与骄傲被现实击得粉碎。
她止不住的哽咽,起初只是细微啜泣,她担心许今朝恐怕只是在外面睡着了,或许出声会把alpha吵醒引过来。
但生理上的反应又哪里是能轻易自控的,宋姣很快呜咽着断续抽泣起来。
oga的哭声与暖黄色的灯光隐隐透出窗外。
又是不知过了多久,宋姣终于缓过精神。
屋外走廊仍是漆黑寂静的一片,她伸手从床垫中摸出早先藏好的小刀,紧紧攥在手中,努力汲取一些安全感。
她赤足踩在地毯上,润白的脚趾缩着,长发披散,像从海里走出来的小人鱼那样轻轻蹑蹑,来到卧室门边,尽量缓慢的关闭它。
许今朝的指纹可以在这栋房子任何一间屋子通行无阻,宋姣这样做也只是获取少少一点的心理安慰罢了。
房门关闭后,她将刀刃向外紧紧贴在胸口,焦虑与恐惧没能减少分毫,被扼住喉咙的窒息感反倒更重了。
宋姣最终把自己藏进了浴室里。
浴室的锁扣可不是电子锁,宋姣将推拉门反锁住,整个人缩进浴缸中,假装脆弱的玻璃门能抵挡住alpha的入侵。
她的脑子里乱糟糟一片,时而想着要和许今朝拼命,时而想着要逃走,时而又回忆起被alpha信息素压制到近乎崩溃的绝望。
惊吓之下,本就病着的她开始发烧。
宋姣没察觉自己的体温在上升,但高热让她的意志恍惚,打开龙头放起了热水。
水没过脚踝,小腿,湿透的绿睡裙裙摆浮起、像大片舒展荡动的荷叶。
宋姣卷起袖口,将手浸入水中。
oga玉藕似的手臂在水面下闪着粼粼波光。
凭什么,她想,自己什么都没有做错,她绝不为做错事的人支付代价。
宋姣的意识逐渐模糊,最终歪倒在浴缸里,昏昏睡去,水汽氤氲着潮红的美丽脸庞。
许今朝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初秋的夜风吹得人通体冰凉。
她已然下定了决心,哪怕先下手把自己的信息腺挖了,也好过失控伤害宋姣。
但现在不是搞这些的时候,她也没有书中宋姣的意志,能亲手毁掉腺体。
眼下许今朝整个人冻得要命,要是在这天台呆一整晚,恐怕第二天她的小妻子就要欢天喜地来给她收尸了。
问题是许今朝怕自己兽性大发,防范工作做得过于到位,尼龙扎带正紧紧把左手手腕和栏杆捆在一起。
她右手在身上摸索了一番,翻出一只防风打火机。
许今朝打着火机,蓝幽幽的火舌在夜风中舔舐着尼龙扎带,很快把它燎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