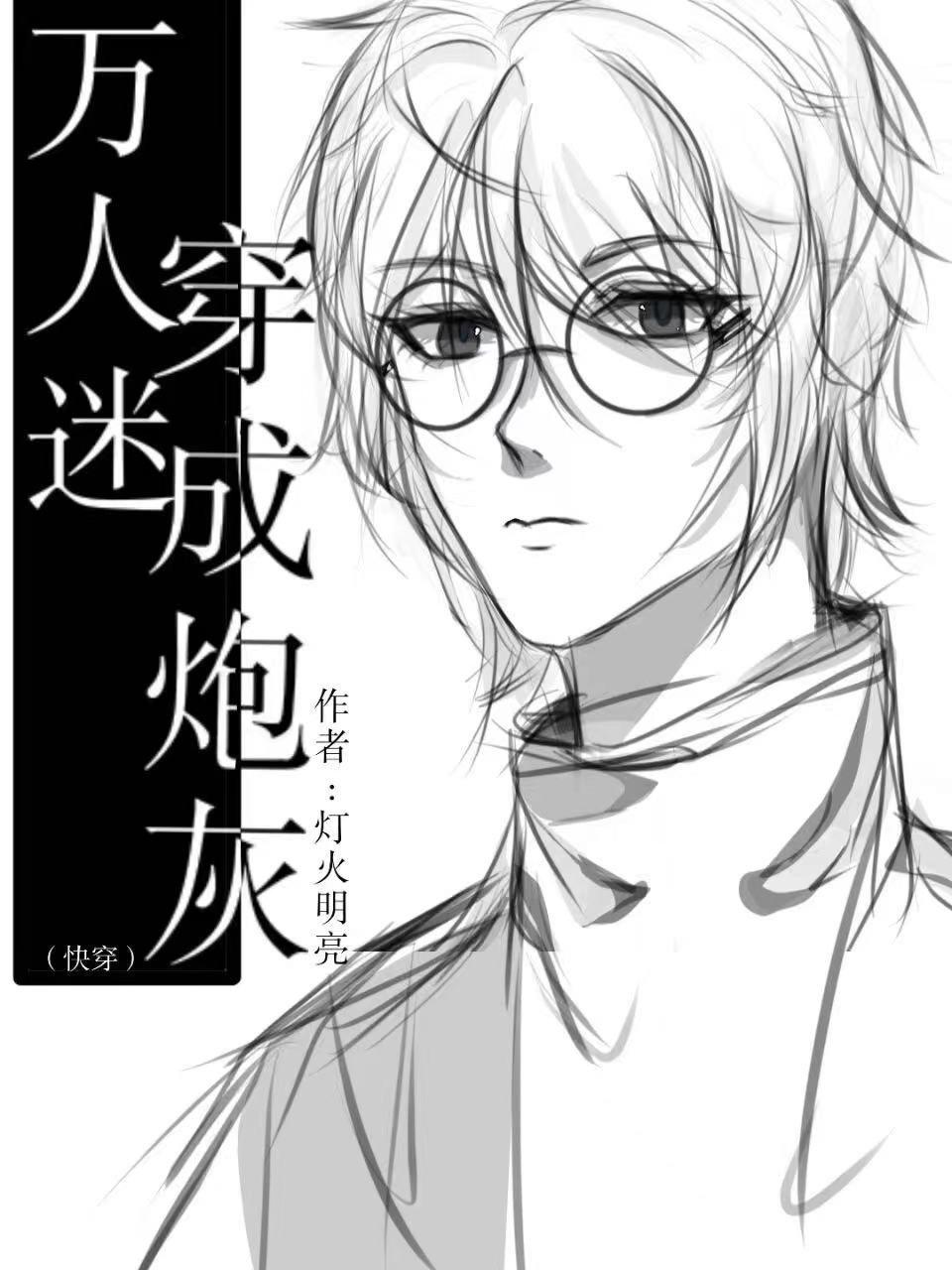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飞花令 > 回归现世(第1页)
回归现世(第1页)
蓝色的光芒铺天盖地,刺的崔琢寒不得不抬手掩眸,等她感受到那光芒弱下去时再睁眼——
温和的阳光、翻开几页的书、玻璃窗外楼下行走的人
她回到了她家书房中。
崔琢寒怔怔垂眸。
她的左手握着一根簪子,也可以说是拆成一半的钗,簪身上雕刻着细纹,其上的绒花很像栀子,七八朵漂亮的栀子簇拥着一捧弦月。
崔琢寒定定盯着栀子和弦月看了一会儿,视线从簪子上移开,落到书桌上。
书桌上翻开几页的书旁,她手机的屏幕不停亮起、消息提示声也响个不停;而书前,一枚暗金色的羽毛躺在那里,羽毛下的金色细链悬着一朵红色小花、一个刻了什么字的薄小木块和一片圆印。
崔琢寒放下簪子,先拿起了手机。
手机上的日期是清清楚楚的二零二三年十月七日,星期六下午四点。她记得她当时正在看文献,然后去客厅接了杯水回来,书前就突然多了片羽毛,然后再一恍惚,人就坐在了那朴素狭窄的马车里。
骆矜说的令牌
崔琢寒试探抬手拿起羽毛,发现那圆印上是镂空雕刻的风信子,而薄小木块上刻着的字是龙飞凤舞的“飞花令”,“飞花令”背后她翻过小木块,微怔。
小木块的另一面刻着一行链接?
这古怪的令牌拿在手中,风信子化作的簪子也好好躺在书桌上,崔琢寒终于确信,一切都不是梦,也不是她的幻觉臆想,她真的被卷入了什么可怕的存在中。
手机还在嗡嗡震动。
崔琢寒放下令牌,把屏幕划开,粗粗扫了下跳进来的所有消息,然后点进母亲的未接通话中,电话只响了一声就被接起,那边的人明显一直守着——
“喂?妈。”
“哎皎皎啊,怎么不接电话呢?”
崔琢寒低眸看着被她放在书上的令牌:“刚刚睡着了,你们打过来我才醒的。你和爸是不是很担心?”
“哎!”电话那头叹气,“这要平时还行,一下不接肯定就是你有事嘛,有啥可担心的?主要啊我和你爸刚刚才发现,这半个月怎么一个电话也没给你打啊?都是你打来的,这年龄大了记忆真不行,可怎么这也能忘?我想不起来怎么你爸也想不起来,哎皎皎,你说要不我俩这次旅行回来去医院看看?别是得了什么病”
崔琢寒耐心地安抚完母亲,挂掉电话,点开几个微信窗口,有闺蜜杜锦亦惊吓为什么结婚忘了叫她这个伴娘但还好现在还来得及,有同事慌慌张张说怎么忘了给她发资料林林总总,她一一回复完并表示现在有事以后再聊。
放下手机,崔琢寒重新看向令牌。
片刻,她抿了抿唇,打开书桌的抽屉拿出自己不常用的一张电话卡,把手机里的换了出来,然后按下一组号码,拨打。
“嘟——”
“嘟——”
电话响了三声,被接起。
两边第一时间都很沉默,大约三秒后,那边传来个清冷的嗓音:“崔玉?”
崔琢寒吐出一口气:“骆小姐,是我。”
骆矜好像笑了声:“记忆力不错。”
在分别上自己的马车前,骆矜叫住崔琢寒,报了一串数字,报完她瞥了眼不远处望着这里的郑小翠,收回视线对崔琢寒道:“这是我的号码。”
现下,骆矜悠悠开口:“刚出来还不到半个小时,你应该还没有和郑小翠打过电话吧?”
崔琢寒愣,迟疑了下还是选择实话实说:“我没有她的联系方式。”
“嗯?”骆矜惊讶,“你留了你的给她?”
崔琢寒:“也没有。”
电话那头沉默。过了好一会儿,骆矜才又道:“要见一面吗?地址可以你定,最好在最近半个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