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千小说网>分居二年一方还不同意离婚怎么办 > 第 61 章 061(第2页)
第 61 章 061(第2页)
陆难轻描淡写,几句话就带过了当时的情况。
林与鹤听着却只觉得脊背发凉。
情绪堆积得太多,反而说不出口,喉咙像是被堵住了,似是过了许久,林与鹤才问出一句。
“……疼吗?”
陆难说:“不疼。”
骗人。
林与鹤想,哥哥之前还说他是小骗子,结果自己都说谎。
刺穿的伤口肯定很疼,一针一针刺破皮肤的纹身也会很疼。疼痛不会因为身体的主人看起来很坚强就消失,它总是客观的,公平到近乎冰冷,即使有人善于消解隐藏,疼痛也一定会存在。
像是看出了林与鹤不相信,陆难又补了一句:“这只是一道疤。”
林与鹤却好像是忽然被惹怒了:“伤在这种地方,怎么能说只是一道疤?”
他很生气,气得声音都有些微颤,情绪突然一股脑地涌出来,莫名的激烈。
陆难却只是望着他,声音依旧低缓。
“宁宁,你身上也有。”
林与鹤微顿,随即就被人握住了手。
温热的微糙的指腹覆在他清瘦的腕骨上方,那片浅红色的地方,当年打留置针留下的伤痕。
男人轻轻摩挲着那片疤痕,与他十指相扣。
他们都带着伤。
陆难的另一只手顺着林与鹤的侧颊向下,捏住那清瘦的下颌,轻轻抬起。他的掌心贴着人脸颊许久,依旧未能将那凉意完全驱散,于是就换了一种方法,更温柔地暖热了他。
笼罩下来的气息太过熟悉,熟悉地让人无法抗拒。
甚至想要更近一点。
林与鹤刚刚还在生气,现在却不知道为什么,闷胀的部位忽然从胸口变成了眼眶。
他们接吻过很多次,之前林与鹤都是因为不会换气才会湿了眼睛,这次却连鼻根都酸胀起来。
所有的情绪缠搅在胸口,理不清,只剩本能。
本能地怀念与眷恋。
许久,等他彻底被暖热之后,陆难才将他放开。
生理的反应对于精神的影响太大了,大到让人很难抗拒,所以等男人伸手为他将眼角湿意抹去时,林与鹤第一次抛开了赧然,带着鼻音,闷闷地说。
“哥哥,你今晚还要工作吗?”
他问:“你要去书房工作的话,我可以和你一起吗?”
陆难又低下头来亲他,亲不够,索性直接将人打横抱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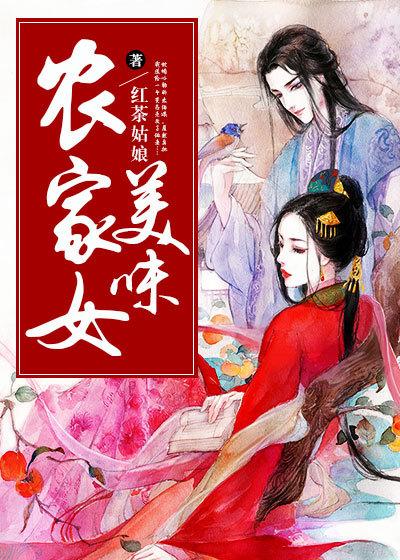

![原来我是漫画里走出的万人迷[反穿书]](/img/3281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