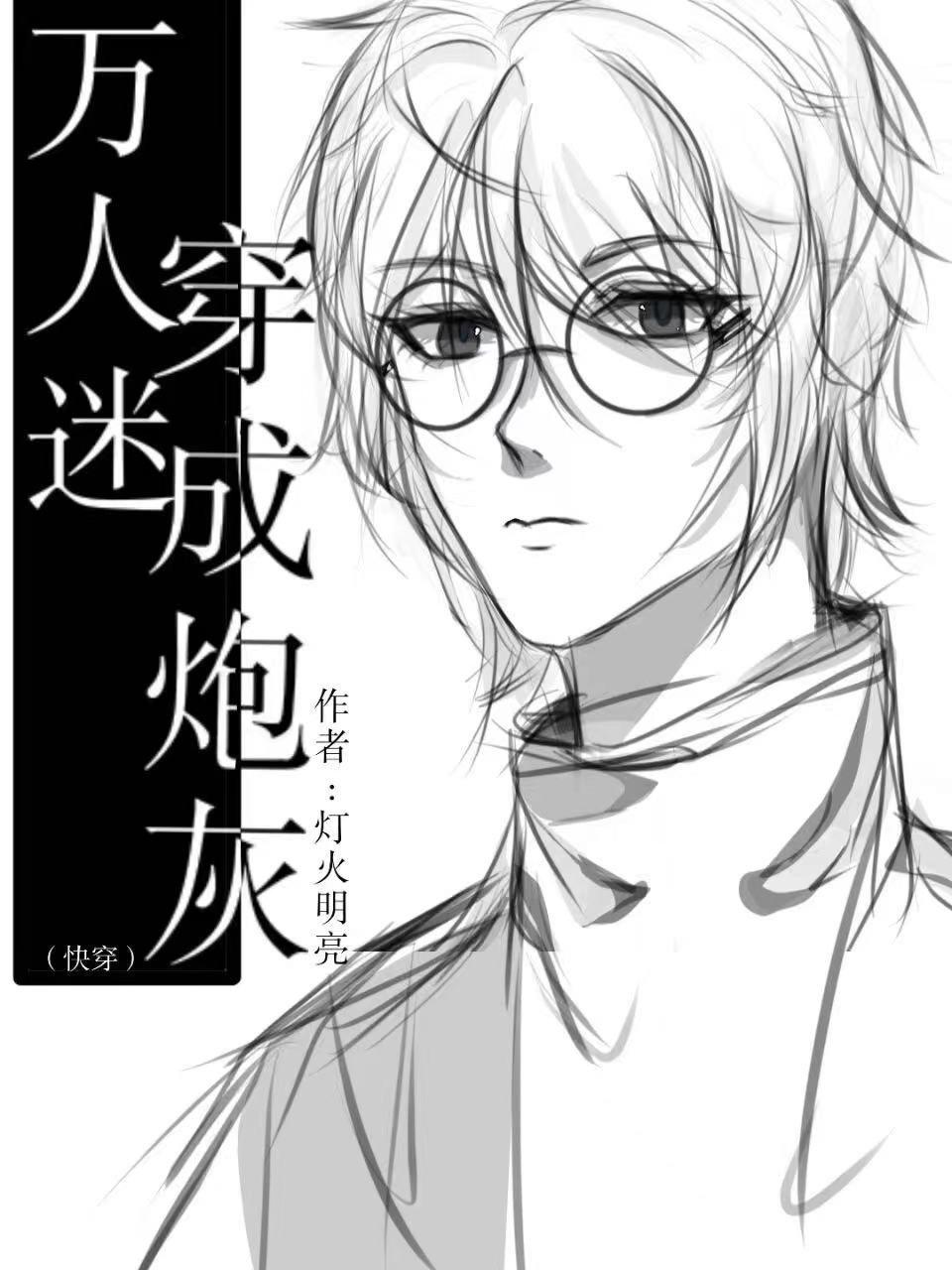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狐媚子需要天赋 > 第45章 尧臣十七(第1页)
第45章 尧臣十七(第1页)
被狐狸捅开的窗户大敞着,如霜的月光照进屋内。
侧躺的小和尚安静地伸出手掌,月光便在他手心叠了薄薄一层。
他捏个指诀,那银纱般的月光旋转着升腾起来,如人世的烟雾一般,缥缈而起,落在窗棂上放置的一片碎瓦上,落地生根,吐出一片圆润的银叶。
和尚轻轻翻了个身,闭目安睡。
瓦片上幼芽轻轻摇曳,抽出纤细的银色枝叶,刹那绽开数朵细小的倒挂铃兰。这花好似一个有五感的人,忽然屈起腰肢,向一旁躲避开去,与此同时,瓦片“咣当”一颤,险些给跳进窗来的狐狸一脚踩翻。
银叶这才抖了抖,重新舒展叶片。
苏奈拖着尾巴,呼哧呼哧地跳窗跑回屋里,眼里尽是火团。
水水水……
真是倒霉,外面没有一处水可以喝,喝不到水,堂堂一只狐狸精就要被烧死了。
苏奈头重脚轻,直接从季尧臣身上踩了过去,窜进厨房。季尧臣霎时惊醒,一个翻身坐起来,点起灯烛,见小和尚也被他惊醒,便抱歉地解释道:“小师父,惊醒您了……”
小和尚眼神微动,欲言又止,季尧臣已披衣,向厨房看:“我方才感觉到一只大老鼠从我床板上跳过去!小师父安寝,我这就去看看。”
厨房正传来阵阵叮铃咣当的响声,这老鼠甚是嚣张。
季尧臣恨极硕鼠,操起墙边棍棒,贴着墙根走过去,却只见一个翻箱倒柜的背影——竟是个人!不是什么贼子,好像是……苏奈,季尧臣手上棍棒一松,心头火起,低声喝斥道:“你大晚上不睡觉,跑这里做什么幺蛾子!”
苏奈转身,脸上通红,额发汗湿,浑似在外面跑了几百圈的模样,可怜巴巴蹲在地上,活像只大狗子:“奴家就想找点水喝……”
季尧臣神色稍霁,仍是嫌弃地皱起眉道:“喝水,你……你昏头了么,水缸在外面!”
如此说着,还是取了只碗,替她从缸内打了水,苏奈接过去便饮,咕咚咕咚地往下灌着,水渗在衣服上了也不管,她一连喝了三碗,才缓过神来,一惊一乍地比划道:“先生,外面的河水变咸水了!”
季尧臣心道,方才开门,门锁都闩着,哪里有什么河水!
“你做梦了吧。”
难怪热得浑身是汗。
季尧臣没好气地收了碗,催她别再三更半夜折腾了,回头一瞧,微微一怔:就这片刻功夫,她身上、头上的汗,竟全都蒸干了,脸上一道一道的红也褪下去,衣摆飘飘,发丝摆动,哪还有半分狼狈模样?
季尧臣端着手上灯烛站定。
灯下看人,果真能添三分颜色。
这蠢笨粗浅的小妇人,在这摇曳烛光的装点下,好似有一瞬间脱胎换骨,虽然穿着是农妇的碎花布衣,却掩不住其风流韵态。妖娆的狐媚相,野蛮的痴傻气,仿佛褪去了些,眉宇间添上几分周正的灵气,若是不开口说话,倒还能装个端庄……
“季先生,奴家——”下一刻,苏奈便毛手毛脚地站起来,一头撞在他下巴颏上,险些将季尧臣手里烛火撞翻,也将他的幻觉全部破灭。
季尧臣扶着下巴,痛苦地倒退了几步,眉毛扭在一起,扬手在苏奈脊背上狠狠一拍:
“你什么你,还不滚去就寝!”
“苏奈,你没买错药吧?”
翌日,小和尚坐在板凳上,将右脚纱布层层剥开,纱布黏连着模糊血肉,伤口非但溃烂破出新鲜血液,好像还扩大了些。季尧臣见了,眼皮便一跳:“怎得小师父服下那化伤丹没用,还越来越严重了?”
“苏奈?”叫了半晌,没人回应,季尧臣回头,见苏奈远远地躲在墙角,两只手难得安分地放在了膝盖上,别扭地笑着,只冲他一个劲摇头。
废话……红毛狐狸警惕地瞥一眼那转着佛珠的小和尚,心道,倘若她知道这就是把她丢上天的神仙,打死她也不敢拿狐狸毛乱搞!
二姊姊说,神仙开了天眼,一眼就能望见她们妖精的原型。在神仙面前,她生怕被揭了身份,或者掐断脖子,自是老老实实的,不敢再打采补的主意。不过她看来看去,那小和尚额头上光光的,好像没有第三只眼,不知那天眼在哪里……
顺着那和尚的侧影看到了腿上血迹,苏奈心虚地摆了下尾巴。
一个神仙,难道连一点小伤也治不好吗?
这个神仙本就奇奇怪怪的。上次见他,他还让乌鸦吃他的脚,一幅半死不活的样子,这次又装作脚伤,八成是故意的。也许这个神仙就是喜欢受痛,好比大姊姊修炼心性的时候用石棱子撞自己的脑袋……反正不关狐狸精的事。
季尧臣瞄着苏奈,只觉得异常,这小妇人,见了俊俏的小和尚恨不得巴巴地往上贴,今日却没精打采地蹲在一旁,怎么?转性了?
便将药膏一放:“苏奈,你来替小师父换药吧。”
谁知苏奈一听,身子一抖,爬起来便窜了:“先生,阿雀娘好像在叫奴家!”
季尧臣目瞪口呆,张嘴欲呵,小和尚手上佛珠一滞,只微微一笑,弯腰撩起水道:“小僧自己来,无妨。”
苏奈推开门,潮热的风扑面而来,破旧的木屋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