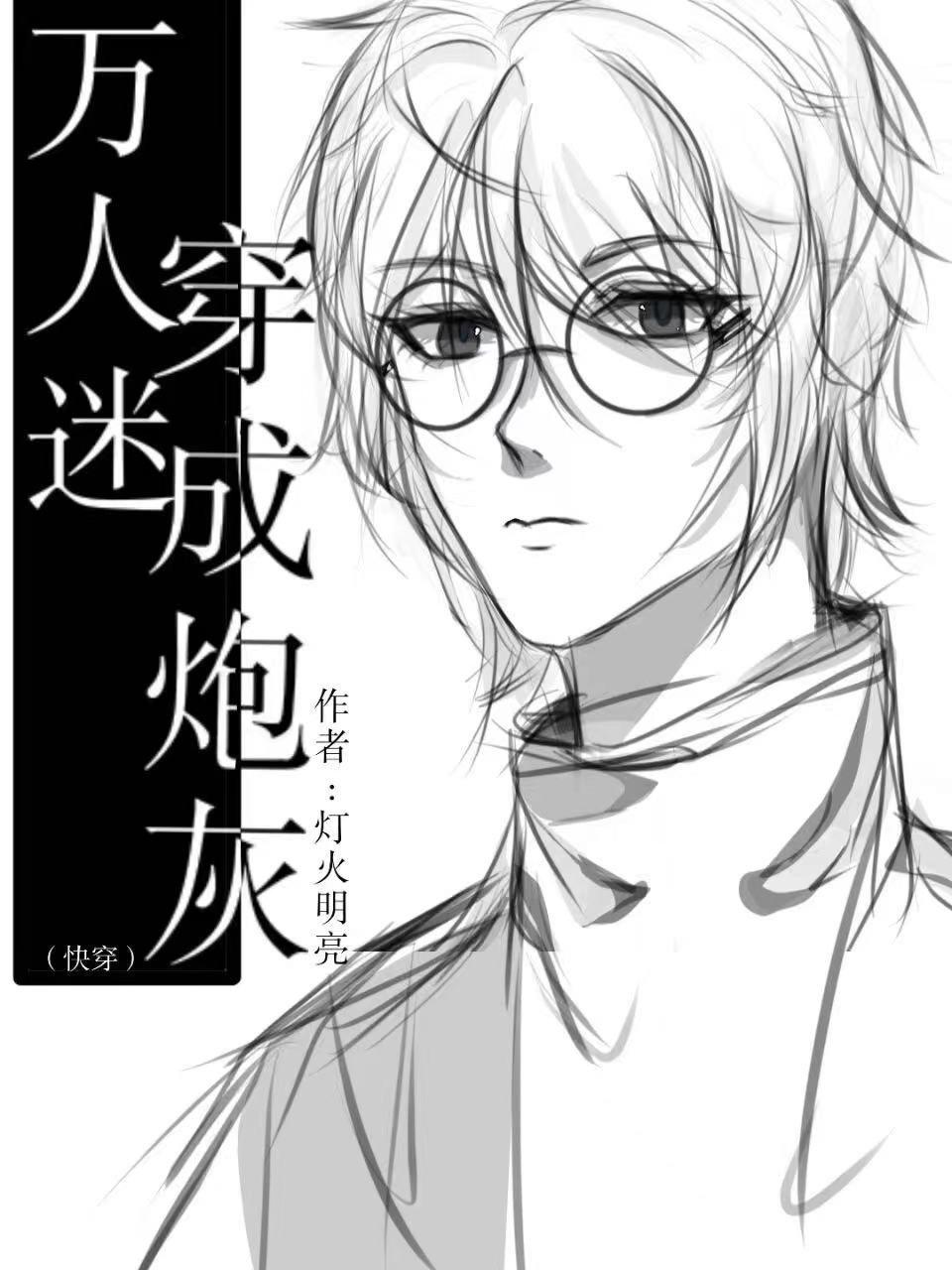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深空降临讲了什么故事 > 第68章(第1页)
第68章(第1页)
难道说“我”被杀死后,那个藏于其中的怪物便直接进入了我的身体,在我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控制起了我的身体,做出了一些我不知道事情?
或许我的这个猜测是对的,若非如此,为什么其他几个人都很自然地将我当成了同类,没有对我产生怀疑呢?
7月5日
你看到了什么了?巨大的机器,跳动的心脏,人们躺在罐子里。
伟大的蟒谷王,你想让我看到的真相是什么?
倘若世界的真实是那般模样?我的存在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7月7日
第七天了,一切仍没结束,我依然利用晚上的时间,坐在窗边的书桌旁,借着台灯的光,用纸和笔做着记录。
窗外是在夜色中变得浓绿阴郁的起伏群山,翠色的草甸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皮,紧紧地包裹着每一寸土地。一排排的白桦树高耸着,似是交叠着的巨大鬼影。
身处于塔拉津的每个地方,视野都很辽阔,能轻易企及到最远的天边,银河从天边落到眼前,近到仿佛触手可及。
梁挽颐跟我说过,天边最亮的那颗,就是天狼星,我望着那颗淡蓝色的闪耀恒星,却并不觉得着迷。
我想起,起初刚到达塔拉津时,我也曾迷失在眼前的美景之中。可此时此刻,我望着窗外的一切,却发自内心地战栗恐惧着,因为我知道,这并非它们最真实的样子,只是一种虚假的表象,是一层不可深入窥探的幕布。
我们人类就像这样,浑浑噩噩地生活在这虚假的幕布之间,毕生也无法看清这个世界的真实。但是浑浑噩噩又何尝不好呢?如果起初就知道这次的旅行会带来什么,我打死也不会来。
直至今日我都忍不住反复思考着那时的情景,甚至无数次设想,如果我们并没有去塔拉津湖的下游该有多好;如果我们没有向本地人打听;如果我们没有产生好奇但显然,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如果,我们根本没有后悔的机会。
现有的科学研究已经表明,穿越时空在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但这仅限于穿越到未来,回到过去却完全不可能。
我知道在我记录这些文字时,那些东西就在我身旁,紧贴着我的头皮,阴森地窥视着我。它们无处不在,只是我们的眼睛无法看到它们。
我决定不再坐以待毙,关于这个世界的真实,关于那些可怕的真相,就藏在塔拉津湖的湖底,我必须找到它,因为它也在召唤着我。
这或许就是我的命运,是我永远也无法逃离的宿命,从我踏上这片土地开始,这个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陶馨雅和林檬檬已经入睡了,我想,等她们醒来时,一定会看到我留下的这个日记本,看到我经历的这些事情。她们会怎么想呢?或许她们会认为我的精神已经出现了问题,觉得我是个疯子。
我有时候也会这样怀疑我自己,但我很确定,我的精神是正常的。我是说,我写下这些文字是为了确保我的精神是正常的,我的精神是正常的,我写下这些文字来确保我的精神是正常的,我是说我的精神是正常的!我写下这些内容来确保我的精神是正常的!我只是写下这些文字来确保我的精神是正常的,我很确定我的精神是正常的!
作者有话说:
评论前五十发红包。
第29章29
梁挽颐的手一抖,日记本便“啪嗒”一声落在地上,自动合上了。
她盯着日记本的牛皮外壳,呼吸急促,整个人都止不住地发抖。
那一行行的文字像是活了一般,从她的眼睛钻入她的大脑,又一下下地敲在她的心脏上。
黄采芹的日记的措辞和用语都非常的清晰明了,可她看在眼里,却有一种晦涩难懂、混乱不堪的感觉。
日记的内容也出现了多次的前后矛盾,可黄采芹却反反复复地强调着自己是清醒的,自己的神智是正常,这巨大的反差冲得梁挽颐的太阳穴突突直跳。
她只觉胃里一阵阵的翻涌,直犯恶心,甚至没法马上认真思考日记提供的信息和线索。
难道日记本有问题?
可是不对啊,这不是陶馨雅指引她来的吗?
她手指哆嗦地开了瓶矿泉水,喝了一大口,才总算稍稍缓了过来。
她弯腰把掉在地上的日记本捡了起来,却不敢再翻看里面的内容。
好在她刚刚看的时候很认真,里面的内容都一字一句地印刻进了她的脑海里。
如果让她用一个词来形容那些内容,那就是,诡异。
梁挽颐闭上眼睛,克制着心底那份莫名的战栗感,努力梳理着线索。
首先,日记一共有四篇,第一篇和第二篇日记存在着明显的矛盾。第二篇日记中,黄采芹甚至明确地表示,第一篇并不是她写的。
两篇日记的角度完全不同,乍一看好像是相互对立的两个视角,似乎是想要让看日记的人去分辨到底哪篇日记的内容是真实的,哪个才是真正的黄采芹。
但梁挽颐思考一番后,却觉得,这两篇日记都不对劲,假设有真的黄采芹和假的黄采芹,那么两篇日记都是假的黄采芹所写的。
原因很简单,第一篇日记看似正常,却处处透着诡异,她在描述她所经历的异常事件时,虽不停地用文字表明,自己是多么的害怕,多么希望那只是一场噩梦。可她的字里行间却透着一种藏也藏不住的兴奋,就好像在期待着什么的到来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