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千小说网>死神的职业有什么 > 锁骨(第1页)
锁骨(第1页)
横滨警方最近头疼不已。
按照惯例,他们向武装侦探社递交了委托。然而那位世界第一的名侦探只是扫了眼卷宗,便原封不动地还了回去,还说这案子没有凶手,直接按自杀结案就好。
警局的一线调查员为此已经堵了侦探社长三天门。
因为江户川乱步的提议根本不可能被死者家属接受,其中一位更是来头不小,乃是横滨的市议员。
三名死者的身体只剩下皑皑白骨,没有一点血肉,用法医的话说,就是高压锅煮过消毒的骨头也不能比这更干净了。要不是还能从牙齿里提取dna验明身份,这桩连环杀人悬案简直一点有用信息都没有。
死者间另一处共通点在于他们陈尸的地方,虽然有的是公寓,有的是汽车旅馆,但都是在封闭的室内。
特务科一时找不出能够造成类似效果的在册异能者。凶手也似乎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谜团。他大剌剌地把一切公之于众,本人则隐藏在人群之中,恐怕正为自己的恶行经由公共媒体所引发的恐惧而自得。
总而言之,七月的横滨,风声鹤唳。
冰块跟玻璃杯撞得当啷响,夏油杰悠悠喝着酒,漫不经心地听着蓝调里一两耳酒保的电话。
因着客人不多,她正跟手机另一头小声地道歉:“没办法啦,店长把我的白班都调到晚上了。说是什么最近男人晚上在外有危险。”
她小心地瞟了眼一个人占据整座吧台的夏油杰:“今天就这么一位客人。没准能提前打烊呢。”
可惜老天没有听到她乐观的祈祷。
快十点的时候,一位冶艳的女士推门走了进来。她精心盘好的发髻一丝不苟,在灯光下泛着润泽的乌光,没有多余的发饰,只插了一枚莳绘的发梳。茜色的色留袖勾勒出她窈窕的身形,行动间下摆微微起伏,仿佛上面大团的牡丹与唐草也随风摇曳。
酒吧里随处都是空位,她偏偏要坐在夏油杰旁边。酒保按她的吩咐送上一杯香槟,迅速识趣地退到一边。
“橙汁?”她细长的眼角向下一转儿,眼波粼粼,抬袖掩住嘴角。
若是年轻气盛的毛头小子,肯定经不住她这样含蓄礼貌的讥讽,撸起袖子就要跟她拼起烈酒来。
再有良知的酒保这会儿也只会煽风点火。毕竟比起实实在在的金钱,谁高兴多管闲事去坏人家的好事呢。
何况,男孩也好,男人也罢,在这事儿上总是不会吃亏的。
夏油杰却跟她见过的男人的反应都不一样。
刚刚跨过成年的青年身上还没褪干净少年人的清爽,又有着年轻人桀骜不驯的冷淡。他似乎对美酒与美人兴致缺缺,因而无论是对方的暗讽或是青睐,都不能动摇自己的节奏。
女士鼻翼翕动,空气中另有一种干冽的气味。
事实上,他喝的也不是橙汁,而是兑了生命之水调制的螺丝起子。
年轻的帅哥不接茬,成熟的美人却抿着香槟频频偷看。于是,两个人相对无言了好一会儿,缩在柜台角落里的酒保尴尬地两只眼睛都不知道往那儿摆才好,只能向上放空,盯着卡座墙壁上老板买回来的提香的复制画。
画中美貌多情的维纳斯裸着一整片优美的后背,无情的阿多尼斯却视她热烈的搂抱于无物,一心要牵着猎犬赶去打猎,几乎把爱神甩到地上。
古董座钟突然弹响半点的钟声,惊了神游的酒保一跳。
也就在这时,今夜的第三个客人推开了店门。
进门的是个清爽的少女,炎热的夏天套了条简单的浅蓝连衣裙,飘动的裙摆下两条新雪一样洁白纤细的小腿,长长的黑发在脑袋右侧扎了个单马尾,还别出心裁地绑了个大大的同色蝴蝶结。
她的身形实在娇小,以至于酒保很是犹豫是否需要站出去查看一下对方的身份证件。再怎么说,他们也是家遵纪守法的经营场所。
不过她很快就不用烦恼了。
少女的目标很明确,径直朝着吧台走过来。
夏油杰替她拉开高脚凳:“要来一杯么?”
少女似乎还没到能欣赏含酒精饮品的年纪。她秀气的鼻头轻轻皱起,摇头挨着夏油杰坐下,熟稔地摘下他杯口切角的香橙。酸甜的汁水在口腔榨开,她的脸色才看起来愉悦了许多。
“菜菜子叫你快点回去,美美子要听睡前故事。”
“你不想听吗?”
少女作势挥起了拳头。
夏油杰从善如流,把杯中的余酒一饮而尽,挥手跟酒保作别。
“哦——那今天讲什么好呢?”他往酒吧门口走去,边走边故意逗人,“让我想想,梅津忠兵卫还是果心居士的故事?”
少女从高脚凳上跳下来,跟在他身边,像只生气的兔子:“按顺序明明轮到了牡丹灯笼!”
等到风铃响了又停,酒吧的门拉开又合拢。独饮的美人醉眼惺忪,问酒保:“刚才的小帅哥是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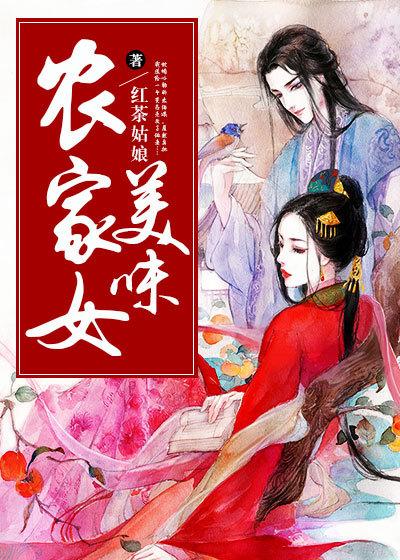

![原来我是漫画里走出的万人迷[反穿书]](/img/3281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