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千小说网>卸甲包的正确用法 > 第60章 相见时难别亦难(第1页)
第60章 相见时难别亦难(第1页)
“下雪了。”
沈羽披着黑色的大氅,站在校场的台子上双手合拢在嘴边,呵了一口气,搓了搓手,没来由的又说了一句:“好大的雪。”
穆及桅一脚深一脚浅的从下面走上来,须发上都是雪花,正巧听见沈羽独自站在那里口中咕哝,朗声嘿嘿一笑,转眼看着茫茫雪地之中还在操练的军士,只道:“你自小生在四泽长在四泽,如此大的雪,怕是没见过吧。”
沈羽没有转头,仍是凝着目光看向远处,微微点头,轻声说道:“确实从未见过。”
“西余的雪,一下,就要大半月大半月的下,此时才只下了几天,待得再过几天,这雪怕要没过膝盖。到时候,咱们也能歇一歇,喘口气了。”穆及桅抖了抖身上的雪,从腰间摸出酒壶,放在耳边晃了晃,唇角一弯:“这酒,都裹着冰碴子,喝起来,可是扎心扎肺的凉。少公可要试试?”
沈羽这才侧目看向穆及桅,瞧着他拿着酒袋子咕咚咕咚的喝着酒,瞧着那样子都觉得阵阵发寒,轻笑只道:“穆公倒真是铁血汉子,便是在如此冰天雪地,还要喝这样的酒。”
穆及桅抹着嘴,打了个酒嗝呼出一口白气:“冰天雪地寒酒,可咱们的血确是热的。”他说着,抬手重重拍了拍沈羽胸口:“沈小少公可是狼首,狼,可不惧苦寒。”
沈羽因着他这动作径自往后退了半步,穆及桅也愣了愣,面露尴尬,扯嘴一笑只道:“哎,与你待得久了,我都老糊涂了。竟忘了这事儿。你可莫怪叔父唐突。”
沈羽眨了眨眼,裹了裹身上的大氅,这大氅对于她来说显得还是有些大了,披在身上松垮垮的:“莫说叔父,做狼首沈羽时间久了,便是羽自己,都觉得自己是个真的男儿了。”她说话间,重重叹了口气,将手从大氅中露出来,对着穆及桅抬了抬,莞尔一笑:“叔父还是将酒给我……”
穆及桅但听此语眼睛一眯,跟个孩子一般将那酒袋子抱在怀中一护:“怎的,如今狼首是要拿走我的酒,不让我喝了?”
沈羽轻笑出声,上前拉开穆及桅的手,竟将酒壶抢过来,在穆及桅那惊异的目光之中径自喝了几口,寒酒入喉,冰凉透心,瞬时觉得周身都冒了寒气,喉咙处凉过之后又似火烧,不消片刻周身都热了起来。她长舒了一口气将酒袋递回去:“好酒。”
穆及桅那惊异转瞬变为大笑,张口将剩下的酒都喝进肚子,皱起眉心看着广阔的校场,轻声说道:“几日前,太子亦已得诏令,眼下,舒余的形势,很快便就要改了。待得春天到来,冰融雪化,就是咱们和那些中州人一决高下的日子了。”他凝目看向沈羽,但见沈羽面上浮起一抹忧虑之色,知她心中不知又因着什么事儿杂乱,低声又道:“可在大宛的事儿,我听也没听明白。何以王子卓回来的时候,是那般模样?真如传闻所言,是被那哥余阖打的失了神志?”
沈羽淡然一笑:“孰真孰假,谁又知道呢?”她摇了摇头:“穆公久经沙场,也在吾王身边呆了这么多年,应也知吾王对哥余之恨,”她顿了顿,又叹了口气:“哥余一族确实叛国,害得我父兄族人皆去,可我……我面对哥余阖之时,却又觉得他可怜,生逢乱世,一国之事,岂是我们这些人一人可成?一族之仇,又岂可用他族之亡替而代之?西迁至此,我有很多事儿想不明白,可秋猎回来之后,我又有更多的事儿想不明白。”她眼神忽晃,说到这些话儿,一张脸都凝重起来:“穆公直言与我,羽是否真当的起这泽阳之公,舒余狼首之位?”
她问完之后,便就瞧着穆及桅,等他答复。可穆及桅却转而看向远处,在飞雪之中伫立许久一言不发,耳边只得呼呼风雪与将士操练之声,时候越久,沈羽的心中就越是烦乱焦躁,却又在她开口欲言之时,穆及桅轻哼了一声,转而一笑,方才那略显混浊迷糊的目光如今变得犀利清明,直视沈羽低声说道:“你既问及此事,那我也便就说说。在我看来,羽之担忧,并非因着军国之事,却是因着心中恐惧害怕。”
沈羽眉目一晃,如同被猜中了心事一般面容微微抽动两下,复又苦笑不语。
穆及桅却又道:“这恐惧害怕,我猜着,一是因为吾王的行事作风与你心中所想大相径庭,二么……”他移开目光,轻叹一声:“是因着公主对你青眼有加。”
“穆公……”沈羽听得公主二字,心头便突突地跳,急忙开口欲言,穆及桅却并未理会,接着说道:“吾王之心,没人猜得准,莫说是你,便是我,都觉惶然可怕。可公主之事,我在军中却听过些许传言,鹿原一战,公主受了重伤。狼首日夜守在公主的马车之中不曾离去。”他说着,转头面容微沉的看着沈羽,目光交杂着复杂的情绪:“我早就同你讲过,有些事儿,你知我知陆将知,可公主与旁人并不知。你可知,一男一女在马车之中,会引得多少侧目?我知羽心思善良,待她如好友。可此事,你却真是做的过了。倘若有一日不可收拾,”穆及桅频频摇头:“那可如何是好。”
沈羽静静听着,穆及桅的最后一句,声音沉重忧虑尽显,随着这沉重的声音,她的心也是重重一沉。可穆及桅却有一句说的不对,她以往待桑洛如好友,可现下,却绝非是好友这般简单。
“吾王如今已立王储,王子卓也在昨日往南疆而去。到了十二月,咱们的公主,便要十八岁了。”穆及桅幽幽说道:“十八岁,便也该寻个夫婿了。”他定定的看着沈羽:“如今王子亦成了太子,公主与王子亦兄妹情深,吾王为保太子根基稳固,定会给她寻个日后有大成之人做夫婿。此人,放眼如今朝中,若不是你,怕也只有孟独了。”
“孟独……”沈羽眉目紧皱,胸口憋闷,“他……”
“孟独此人你我都见识过,手腕凌厉狠绝,可他的龙弩卫势如破竹,且只听吾王令从未懈怠。如今年过三十还未娶妻,”穆及桅叹了口气:“可若真是如此,倒是可惜了公主。”旋即又笑:“若你兄长沈泽未死,想来,倒也真是个绝佳人选。昔日,吾王也对他甚是喜爱,甚至还玩笑中与你父提过此事,可惜……”
沈羽越听心中越乱,又听得兄长的名字,这烦乱之中又添上一笔浓重的愁绪,若非战乱若此,桑洛,竟可能是她家嫂。孟独,孟独那样的人,又怎么配得上公主,又哪里及得上自己兄长之万一?如今她对桑洛动情,还如何能对眼下形势冷静分析?
但即便是她心中万分难过不情愿,又能如何?莫不真的要耽误公主一生,她才安心?
许久,沈羽沉重的握了握拳,轻声问道:“穆公,可有法子帮我?”
“帮你?”穆及桅沉吟片刻,将以往提过的话又提起来:“我帮不了你,现下帮得了你的,怕只有离儿了。”他看着沈羽的面上已然染了霜色,沉声又道:“离儿过几日便十四岁了,你或可以她还年幼为由,再拖个两三年。只盼着两三年后,战火平息,可解甲归田,那便最好。”
“解甲归田,”沈羽自嘲一笑:“穆公昔日还说羽是将才,要卸下这身甲胄,怕是难了。如今,怎的又提起这四个字?”
“见惯沙场,方知平淡不易。”穆及桅拍了拍沈羽肩膀:“你父在天之灵,定也盼着你日后能嫁个好人家,开枝散叶相夫教子。”他抬步欲走,却又停下步子,不放心的又嘱咐了一句:“离儿的事儿,宜早不宜迟,你最好,早些禀明吾王。断了公主的念头。”言罢,转身离去。
断了公主的念头?
沈羽看着穆及桅的背影怅然一笑,公主的念头好断,可她自己的念头又如何断?
黄昏时分,朔城传来急报,只道中州大羿军这些日子总在边境扰民,请吾王令,派军前往。沈羽瞧着那皱巴巴的纸张,神色更加凝重。战事吃紧,千钧一发。她在账中坐到深夜,双手放在火边靠着,目光一直瞧着那跳动的火苗,穆及桅之言在如今瞧来却是一条好计策,可她沈羽,不想误了离儿,更不想欺骗桑洛。但若什么都不做,结局恐怕真如穆及桅所说,吾王赐婚,到时候穿了帮,她一死无妨,可桑洛……
她目光复又移向那前方传来的信,双目微眯,抿了抿嘴,在心中做了个决定。转而起身,披上大氅,也不牵马,径自往狼绝殿而去。
明日一早,她便要往一道门向吾王请旨,亲往朔城督军备战。此一去,等的开春大军再战,尚不知还会否能回返皇城。可她若不去,等待自己的,是更加沉重的心思之事。眼下,怕也只有这个法子,可得双全之法。
站在狼绝殿前,她那黑色大氅上落满霜雪。看着雪夜之中的轮廓,目光却又往西北方向而去。
主意已定,心意已决。
她在此时,却倍加思念桑洛。
她挪了挪步子,却又转回来。转回来,却又往一道门的方向挪了挪步子。踟蹰徘徊许久,叹了口气。
过了今夜,不知何时还能再见桑洛,再见桑洛,或许她已为人妻,有了子女。想及此,她心中绞痛,便是连气都喘不上来。
沈羽紧紧地握着拳头,她想在离去之时,再见见桑洛,哪怕就看一眼,看一眼也是好的。
作者有话要说: 说好的互动肯定绝对一定就在下一章了没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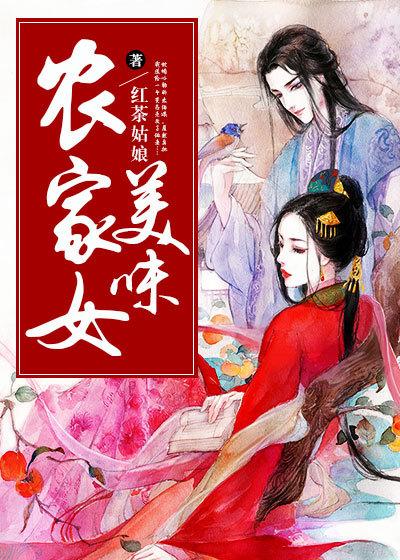

![原来我是漫画里走出的万人迷[反穿书]](/img/3281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