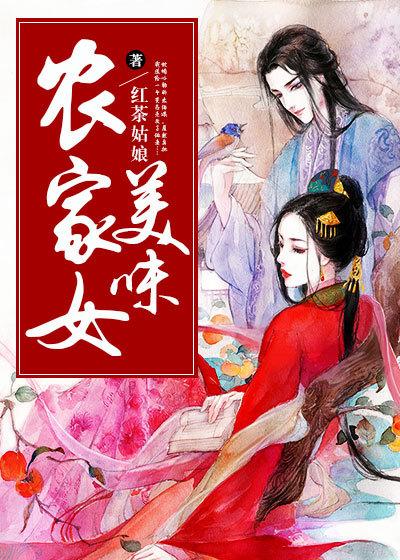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闻君有两意 > 福禄寿(第1页)
福禄寿(第1页)
连阴了几日,雪终于落下了,落了一个白日,又落了半个夜晚,夜半时,雪停了,彤云散尽,明月如镜。水月庵的妙茹行完佛事后,走出佛堂,见院中积雪,厚及盈尺,为月光浸着,白若素缟,便踏雪走过院中,推开寺门,立在门内,看了一眼门外的世界,只见冷月千山,天青地白,心中不觉一旷,这人间啊,白茫茫一片,干净得让人陌生,然匿了往日的啼鸟,又觉有些空寂。忽然树上的一捧积雪,无风自落,哗然有声,在静夜中,格外明晰,妙茹一惊,阖上了寺门,回到禅房里,点燃油灯,抄写了一遍心经后,吹灭了灯,卧睡,却一时无眠,窗子是白的,不时有积雪坠落的声响,愈发寂静,寺外的鸟儿去哪儿了,被大雪掩埋了吗?也许没有鸟啼还是好的,被掩埋的鸟儿,那啼声会让这雪夜格外的悲凉吧。记得幼时在家,阿母说寒号鸟,总在下雪时悲喊:哆啰啰,哆啰啰,下雪冷死我,明天就起窝。可下雪时,鸟儿总是静默的,自己从没听见过寒号鸟的叫声。几念后,妙茹觉心中微澜,便默念起了心经,不知不觉中睡去。
晨时,妙茹去院里打水,见雪上的足迹,宛如昨夜,一刹那间,觉得这足迹,倒不像是自己走过的,是另一个人,另一个自己,留下的印记。妙茹打好水后,在厨房煮粥,忽闻一阵人声,倒是有些好奇,这么大的雪,还有谁上山来庵。不一时,锅里的米还未熟,一个老者走了进来,妙茹见之,不免一惊,原是从前家中的管家。老者见妙茹正拿着火筒吹火,一时倒也难语,只是默然的看着,倒是妙茹起身对老者行了一道佛礼,老者见此,眼角一湿,眉目一哀,悲声道:小姐,夫人不行了,你回家看看吧。妙茹闻了,心头一惊一恸,然还是冷着说:我既已出家,家中事与我何干。老者低下头去,低声道:夫人一直念着你,难以瞑目啊,求小姐回家一趟吧。妙茹见老者的哀求,心中也是一悲,便道:我去问问师傅吧。妙茹来到佛堂,见师傅正跪在佛像前诵经,还未开口,师傅回头看着妙茹道:我都知了,你去家中一趟吧。妙茹看着师傅,沉默了片刻,说道:我已是出家人,又粘那些事做甚。师傅看着妙茹,一叹道:你虽已出家,然世人还在家中,成全他人一场,亦是善行,有何不可?妙茹听了,垂下头去,嘴唇抖着,嗫嚅了声:可。却再难他言。师傅又说了声:去吧。便回头诵起经来。妙茹退出佛堂,来到厨房。对老者言道:等把师傅的粥煮好了,我随你去吧。粥煮好后,妙茹盛到钵里,去与师傅言,粥煮好了,弟子去了。师傅点了点头,妙茹回身,走了出去。
下山时,老者言,雪深路滑,让妙茹坐竹舆。妙茹却道:哪有出家人坐轿子的道理。随即披了棕衣,套了齿屐,步行下山,雪路难行,众人行了半日,还未到山脚,虽套了齿屐,然妙茹的僧鞋裰角,还是被雪浸湿了,可妙茹倒不觉。想起阿母,快要死去的阿母,甚至此刻已死的阿母,妙茹一阵茫然后,心里到底一悲,想翻起些幼时在家的事,却发觉无从记起,只记得昨夜的寒号鸟,其他的旧事都随家飘落了。八岁那年,刚从家里来到水月庵时,初时的夜晚,有时梦见自己死了,有时又梦见阿母死了,梦中哭了出来,却不知是为自己而哭,还是为阿母而哭,过了那段时间,到了此时,倒也哭不出来了。到了山脚,管家老者说:下山了,还有一个多时辰就到家了。妙茹听了,倒不觉离家近了,反而觉得离庵远了。到了城郊,路边的住户多了起来,路过一户人家时,竹篱柴门内,一株山茶红若云霞,一个穿红棉袄的女孩,站在树下,摇着积雪,雪落下来,打在头上颈上,女孩也不管,倒是家里的阿母见了,站在檐下叱道:疯丫头,发疯了。女孩听了,笑道:这雪把花压着了。妙茹见此,寒着的心倒是一暖,看了那女孩几眼,又随着众人前行离去。
不一时,城门的云楼已在眼中,妙茹走入城中,人群的喧躁,到让妙茹心里一慌,随着管家来到家中,到宅门时,妙茹见门上还未挂上白灯笼,心头一轻又一重。家仆推开了门,家中一片哀寂,不闻人声,管家急匆匆的带着妙茹,来到阿母的卧房,房内立满了人,都是亲眷,妹妹阿芸坐在床沿上,握着阿母的手。众人见妙茹来了,纷纷注目,又暗暗的一阵悲然,让妙茹走到阿母跟前,阿母闭着双目,嘴里却念叨着什么,管家站到阿母前,躬着身子说道:夫人,阿茹小姐回来了。阿母似未听见,依旧念着胡话,阿芸握着母亲的手,凑到耳边说道:娘,姐姐回来了,姐姐阿茹回来了。过了片刻,阿母才微微睁开眼目,空洞的看着前方,念念的喊道:茹儿,茹儿。妙茹见此,心中一悲,弯下腰去,握住了母亲另一只手,想喊一声娘亲,却哽在喉头,说不出来。阿母看着妙茹,目光也有了丝意识,妙茹看着阿母的眼睛,知阿母认出了了自己,阿母嘴唇张开,却无语声,眼泪倒簌簌而落,妙茹见母如此,也哭了出来,片刻后,阿母眼闭泪竭,口鼻的气息绝灭了,只有手还握着妙茹的手。妹妹阿芸见母气绝,悲喊道:娘。妙茹也想喊一声娘亲,却还是无法出口,只觉阿母的手变僵冷了。
阿母丧事,由亲长操办,灵柩停在宅府,请了僧道置办丧仪,亲长们劝妙茹留在家中,待阿母下葬后,再回庵去,阿茹却不置可否,然今日已晚,又下了大雪,便留在了家中。亲长见妙茹姐妹皆是女子,阿芸待字闺中,妙茹又是出家人,便也不要她们守灵,由族里的子侄辈替之。夜间,仆人带妙茹来到卧房,妙茹坐在房中,院里的鼓锣声,隐隐传来,妙茹想起阿母那冰冷的手,便在桌案上摊开随身所携的一卷心经,跪在经前,念起往生咒来,为阿母念的。不知念了几遍时,有人扣门,妙茹起身开门,见阿芸站在门外。姐姐,阿芸喊道。妙茹却不知如何回答,便行了一道佛礼,让阿芸走了进来。阿芸来到房中,看着妙茹说:姐姐,我怕,今晚我和你睡。妙茹看着阿芸,犹豫了片刻,说道:你怕什么?阿芸:我怕这般一个人住,阿母走了,我只有你了。妙茹道:我也要走的。又欲说:世人谁不是一个人生,一个人死的。然想起自己和阿芸是双生子,便停住了。阿芸拉住妙茹的手,说道:姐姐,你留几日,为我留几日,可好?说着,又哭了出来,妙茹见此,心头一酸,半是犹豫,半是怜悯的点了点头,看着阿芸道:你先睡吧,我还要行功课。阿芸松了妙茹的手,坐到床沿,妙茹又跪在案前,念起经来,念的却是心经。
经念了多少次,心也慢慢安宁了下来,妙茹见阿芸已睡着了,便吹灭了灯,到床榻上睡下。忽然在黑暗中,听见阿芸说道:姐姐,你恨阿母吗?妙茹惊了一瞬,只觉自己的手,被阿芸握住了,阿芸的手也好冷,妙茹叹息一声,说道:不恨,为什么要恨她。阿芸:可阿母死的时候,你都不愿喊她一声娘亲。妙茹:我是出家人啊!又听见,阿芸啜泣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彼此的沉默后,阿芸又道:也许该出家的是我,就因为你比我早出生那么一点,便把你送去姑子庙,太不公平了。妙茹道:这是我们各人的命运,也是我的佛缘,没什么公不公平的。阿芸:可我亏欠你的太多,我们幼时病弱难医,阿母信了他们的话,说送去出家,我们才能活下来,你出家了,可我活下来了,这是我欠你的。妙茹一笑:若真是如此,我愿三世出家,已生善报。阿芸:可你不觉得苦么?妙茹:我看你们红尘里的人才觉得苦呢,不要胡思,睡了吧。夜间,妙茹却做一梦,梦见庵里不知何时长了一株山茶,自己在树下摇雪,为师傅责骂了一通。
清晨,阿芸醒来时,妙茹已起了多时,正跪在案前默诵着佛经,阿芸见此,便也不打扰妙茹,整理了一下衣裙后,静静走了出去。没过多久,阿芸托着两碗面条来到房里,妙茹还在念经,阿芸便将面条置在桌上,也跪在妙茹身边,双手合十,跟着妙茹念起经来。妙茹见此,看了阿芸一眼,依旧诵着经文,念完后,有些欣喜的问阿芸:你也会念这金刚经。阿芸一笑:阿母教的,其实只会念金刚经和心经。妙茹道:金刚经是佛胆,心经是佛心,在家人念这两部,也足够了。阿芸道:阿母会念的倒是多,我是懒,不愿学罢了。妙茹听了,倒也无言语。阿芸又道:姐姐吃早饭吧,素面,我陪你一道吃素。吃面时,阿芸咬着面条道:姐姐,光吃素,不苦么?妙茹:不苦。见阿芸又欲言,便道:食不语,寝不言。阿芸一笑道:昨夜,姐姐不也言了么?妙茹听了,也不搭话,低下头去,默默的吃着面,阿芸见此,也不再言语。
食完早饭后,妙茹欲行功课,如庵中一样。阿芸却拉着妙茹的衣袖道:姐姐,我们去后园子逛一下吧,看你还记得吗?妙茹道:出家人,有什么好逛的。阿芸愈发拉着袖子道:那你陪我去逛逛。妙茹受邀不过,便随着阿芸来到后园,园中的布置,和记忆中的一样,无多变化,记得那时,初到庵中,几度梦里回到家中,回到家中的那喜悦之情,浸透了心神,是那么真实,以致梦醒后,犹然在心,仿若真的回家了一趟。阿芸和妙茹来到了一间水榭里,阿芸扶着竹栏,看着水中的锦鳞道:还记得吗,那时我们每到雨天,便骗桂花糕来喂鱼。妙茹想起旧事,心头一动、一悲,却淡然言道:忘了。阿芸看着妙茹,有些悲哀,又有些同情,说道:记得幼时你走了,我嚷着阿母,要去看你,阿母却说,你忘了我们,还少受些苦。妙茹道:是的,她是对的,你们忘了我,也少受些苦。阿芸道:可我没忘,阿母也没忘。妙茹道:可我忘了。却也心知,自己是受不了那苦,才觉得忘了。在园里,逛了半日,亭台草木,依如梦中,却没了梦里的欣喜,反而有些悲哀,妙茹便道:逛了半日,也乏了,回去吧。阿芸随妙茹回到房中,又吩咐丫鬟,去厨房安排几样精致的素菜,妙茹坐在梨木椅上,取下念珠,默念起经来,阿芸看着闭目诵经的姐姐,不由得想起每晚念佛的阿母,心里倒有些悲寂。没多久,饭菜送了上来,冬时少有时鲜,除了两盘冬笋、萝卜,其他几样倒都是酱菜,妙茹见了,对阿芸说道:两人哪里吃的晚这么多样菜,明日叫厨房少安排些。阿芸见了,本有些嫌菜肴不清爽,听妙茹说到,便连连点头。阿芸夹了几筷子菜后,对妙茹叹道:姐姐,你走后不久阿母也开始吃素了,我本也想吃素的,唯独戒不了螃蟹,才开荤的,吃了那么多螃蟹,如来佛祖说不定要我下辈子投生螃蟹的。妙茹看了阿芸一眼,停了片刻,说道:不可拿佛祖戏谑。吃了一口米饭后,又道:螃蟹性冷,倒不可多吃。说完,便又埋头吃饭,不再和阿芸搭话。
饭后,妙茹盘坐在案前,对着那卷心经,行着功课。阿芸见此,走了出去,又拿着两个坐垫回来,对妙茹说道:姐姐,家里没有蒲团,不,阿母倒有一个,只是不好拿,就拿这垫子将就下吧。妙茹接过坐垫,见是缎面的,一针一线的绣着花叶鸟鹤,言道:倒是可惜了这精致。阿芸也拿着坐垫,随着妙茹盘坐着,说道:姐姐,这几日我也随你学佛吧。傍晚时,阿芸扭扭捏捏的伸了个懒腰,对妙茹说到:姐姐,吃晚饭吧。妙茹摇了摇头:出家人过午不食,你去吃吧。阿芸一笑:这倒忘了,阿母信佛后也不吃晚饭了。说罢,也忍着疲乏,随着妙茹又静静的盘坐起来。晚间,妙茹见阿芸还盘坐在身边,虽时候尚早,也起身对阿芸说道:起来吧,睡了。阿芸听此,还迷糊着,过了片刻才清醒过来,手酸脚软的挣挫起来,脱了外衫,钻入被子里。妙茹站在床榻边,看着阿芸,犹豫了片刻,也脱掉了长裰,吹灯入睡。突然间,妙茹觉的自己的手又被阿芸握住了,听阿芸道:姐姐,每日这样坐禅,不累么?妙茹沉默了片刻,才说道:不累,睡吧,寝不言。阿芸:好吧。盘坐了大半日,阿芸也真的累了,不一会儿,已然睡去。妙茹还未入睡,任由阿芸握着自己的手,突然间想起了阿母,她也学佛了,也吃素了,是因为自己么?何苦,何必。既舍了自己,忘了,倒还少受些苦。
过了几日,妙茹与阿芸,寝食同处,阿芸随着妙茹坐禅,妙茹有时也随阿芸家中闲逛,前院的白事倒不需姐妹操心,与妙茹处久了,阿芸觉得姐姐又回来了,犹如儿时一般,有时倒忘了阿母已死。那日,阿芸知妙茹早起,睡前暗自决心,要和妙茹一道起来,无奈每日坐禅太累,直到巳时初才醒了过来,穿好衣衫后,看了眼漏箭,不由惊道:阿弥陀佛,怎睡到此时才醒。妙茹听了,心里倒是忍不住一笑。阿芸又道:姐姐,我洗漱后就吃早饭吧。妙茹点了点头,阿芸道:吃面,还是吃粥?妙茹道:吃粥吧。阿芸回来时,拿了一瓶玫瑰露,猩红的玻璃瓶,对妙茹道:这还是阿母送我的玫瑰露,说是西洋国的,一直舍不得喝。妙茹和阿芸,看着那玫瑰露,想起阿母已死,物存人亡,不免各自一悲,阿芸之悲是因母亲,妙茹之悲,一半倒是怜悯阿芸。粥送上来了,滴了几滴玫瑰露后,殷红如血,妙茹尝了口,说道:太甜了。阿芸也道:太腻了。然因是阿母所赠,不愿弃掉,倒也勉力喝完了粥水。吃完粥后,阿芸道:姐姐,那粥太腻了,我们喝茶去吧,我学过茶道,又埋了一坛春天的无根水。说着,便拉着妙茹去花园,挖那坛藏水。
阿芸到花匠处,拿了柄花锄,在一颗银杏树下,刨了多时也不见水坛,正着急时,忽闻身后有人喊道:芸妹在找什么呢?阿芸回身一看,笑道:来得正好,春天埋的那坛无根水,找不到了。那人走来,妙茹见那男子,觉得有几分面熟,却又记不得了旧交了,男子看着妙茹,认得出来,前些天在舅母的房里见过,想起幼时之人,眼前的妙茹却让人陌生,男子也有些尴尬的对妙茹一笑,不知该作何称呼。阿芸见此,拉着妙茹的手说:姐姐还记得孙璞表兄吗?小时候老来我们家玩,却老是分不清你和我。妙茹听了,对孙璞行了一道佛礼,孙璞也急忙还礼。阿芸道:你怎么逛到这园子来了?孙璞笑道:外面刚磕完头,法师们让大伙休息会儿,我来园子清净清净,等下还要去上香。阿芸把花锄交给孙璞,说道:你挖吧,我找不着,记得当时我们是埋在这树下的。孙璞笑道:我亲手埋的,只有我挖得到。说着,便挖了起来,不几锄,已找到了坛盖。孙璞将无根水端上后,阿芸道:去我房里煮茶啊,表哥你也一道去吧。孙璞笑道:你舍得煮明前的那罐雀舌就去。阿芸笑道:当然了,不过你是托姐姐的福。妙茹看了看孙璞,指着前面的亭子,说道:那亭里,石桌石椅都是现成的,去那亭子煮吧。阿芸道:可那人多眼杂,倒难静品。妙茹道:人多才好啊。三人去了那亭子,阿芸吩咐丫鬟将泥炉铜壶拿来,又道:杯盏我自己去拿,旁人倒分不清。妙茹道:我和你一道去吧。
杯盏取来了,两支越窑的白盌,一支宜兴的紫砂盏,阿芸将白盌放在妙茹的面前,又将紫砂递给孙璞,孙璞道:为何你们是越窑的瓷盌,我是紫砂?阿芸笑道:越盌之白洁宜女子,紫砂之蕴藉适男儿。水沸后,阿芸将茶洗了一道,才将茶水分入杯中,期待的看着妙茹饮了口,问道:姐姐,觉得如何。妙茹道:出家人,哪分什么好茶坏茶,皆是一样的。孙璞却道:无根水泡出的,香气到底轻浮些。阿芸看了孙璞一眼,笑道:倒便宜你了。又看着妙茹说道:姐姐,还记得幼时他分不清你我的事么?妙茹低下头去,说道:有吗?阿芸笑道:幼时,大伙都分不清你和我,所以阿母就给我带了一枚玉弥勒,给你带了金子长命锁,让大伙见物识人,后来我们捉弄大伙,我带你的长命锁,你带我的玉弥勒,孙璞表兄的发簪被我弄折了,反倒去阿母那里,告你的状。妙茹听了,微微一笑:幼时不懂事,提他们做甚。孙璞听了,脸上微红,喝了口茶后,放下了杯盏,言道:我去前院了,要上香了。孙璞走后,妙茹阿芸坐在亭内,阿芸又添了三次茶,妙茹道:茶伤脾,够了吧。阿芸道:姐姐,觉得孙璞表兄人怎样?妙茹道:我离家久了,怎知道?阿芸脸色晕红了一丝道:阿母生前将我和孙璞表兄订了亲。妙茹道:一道长大的,到底知根知底,是件好事啊。阿芸脸又红了几分,言道:可。却欲言又止,只是低声道:可阿母看不见了。
夜间,妙茹与阿芸休了功课,睡时,阿芸握着妙茹的手道:姐姐,我小时候带的是玉弥勒,出家的应该是我。妙茹道:最后不是混着带了嘛,我是姐姐,出家的当然该是我,我并不觉得苦。阿芸道:可我觉得你苦啊。妙茹道:我也觉得你们在家有那么多烦恼,反而觉得我是幸运的。阿芸:姐姐,你真的要一个人过一辈子么?妙茹道:我是出家人,当然要如此。阿芸道:可我听说,你们的阿难菩萨,愿为一个女子,化身石桥,受五百年日晒,受五百年雨淋,只为她从他身上走过。妙茹一笑,说道:阿难陀尊者,堪破情障,岂会如此,多是世人的杜撰吧,佛经记载,倒是有一个女子,爱慕阿难陀尊者,发誓要嫁给他,佛祖答应了那女子,不过要她先出家,女子出家后,得佛经指引,看破红尘,知自身痴迷,斩断□□,最后得了阿那含果。阿芸道:可我还是喜欢化身石桥的阿难。妙茹:睡吧,夜深了,明日要送她,送,送母亲灵柩去祖茔,还要早起。阿芸睡着了,妙茹还醒着,她觉得自己似乎原谅的阿母,也与那时离家不久的自己,和解了,幼时的纷纷往事,之前无从记起的,都浮泛起来,也有今日遇到的幼时的表兄,妹妹嫁给他,似乎也成了自己的心愿,尽管这非出家之心所能愿想的。可刹那间,庵中的师傅又让她起念,念起,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不可得,可妹妹握着自己的手,却是温暖的。
阿母出殡时,妙茹陪阿芸坐在马车里,阿芸穿了孝服,带了孝帕,一路倒也无话,行了半日,到了祖茔,下了马车,只见白压压的一片人,有举幡的,有托纸物的,有抬棺的。落葬时,在主事亲长的吩咐下,妙茹扶着阿芸,去灵柩前磕头上香,阿芸见阿母的棺椁落入穴中,为一捧捧泥土,渐渐掩埋了,念起阿母生前,想到阿母生后,心头一痛,大声哭喊了出来。妙茹见此,心头也是一悲,也随着阿芸跪下磕头,上了三炷香,强收住了眼泪。落葬后,余事由族中男眷打理,女辈倒先回府了,阿芸痴痴的看着母亲的新坟,不知不愿回去,还是妙茹把阿芸拉上了马车。马车上,帘子放下了,阿芸匐在妙茹身上,又大哭了起来,妙茹亦无言语安抚,只是抱着妹妹,方才强收住的泪,此时倒默默流了出来。到了家中,妙茹送阿芸回房内,看着泪痕阑干的阿芸,有些不忍的说道:阿母之事已完了,我也要回去了。阿芸听了,本已干涸的泪,又流了出来,哭道:姐姐别走,我怕。妙茹握住了阿芸的手,沉默难言,过了片刻才收住心,说道:我出家了,当然要回庵里去。阿芸哭道:那你还俗吧,回家吧。妙茹道:傻丫头。阿芸哀道:那你再留一晚,再留一晚好吗。妙茹看着阿芸,点了点头。夜间,阿芸睡前还是握着妙茹的手,过了不久,妙茹听见阿芸又哭了起来,便唤了声妹妹,却发现阿芸已睡着了,是梦中在哭,不由得握紧了阿芸的手,心中一悲。
次日,妙茹离家归庵时,阿芸送出了家,又送出了城,还是不舍,妙茹道:回去吧,离家已远了,就送到这里吧。阿芸又拉着妙茹的手道:那姐姐,到时我来看你。妙茹正要点头时,身边驶过一辆马车,马被车夫狠狠的抽了一鞭,那鞭打皮肉之声,击入心耳,妙茹一惊,看了看那行过的马车,听了听人群的喧躁,收回了手,对阿芸行了一道佛礼后,转身离去,一直不敢回头。离城远了,离世人远了,妙茹觉得心自在了些,路过来时那个穿红棉袄怜花摇雪的女孩,那个院子时,发现院里空空,山茶花落了不少,女孩已不在。回到庵中,师傅依如离开时那般,在佛堂念经,妙茹见此,心忽然觉得定了些,经过这些日陌生的旧念,庵里那个熟悉的新生的自己,又回来了。
妙茹回到庵中,课业如旧,行语如常,有时夜间颂完经后,走到院中,回到禅房,也会想起阿芸,此时便抄写心经,为她祈福。开春时,阿芸来了,带了一干随仆,几担物品,说要在庵中住上一月。妙茹见着妹妹,即是欣喜,又是心忧,怕人多口众,扰了师傅清净,便对管事的家仆说,让他们且下山去,三日后回来接阿芸回家。阿芸听了,急得跺脚道:一月后来吧。妙茹道:那七日后来吧。阿芸又道:十五日吧,好吗?妙茹看着阿芸,故作冷言道:那你此刻就回家去。阿芸见此,哀叹了一声道:那就七日吧。众人走后,妙茹看着留下一地物件,说道:你带这么多东西来干吗?阿芸一笑:给你和师傅啊。妙茹道:我们出家人岂要这些东西,以后不可如此。阿芸连连点头,走到一盒竹收纳前,掀开盖子,捧了一块糕点道:姐姐,尝尝吧,昨日刚做的云糕。妙茹道:不用,你忘了,过午不食。阿芸一笑:这倒忘了,明早吃吧。便把糕点又放了回去。这时,一位常来庵中送柴的老樵夫走了进来,背着一捆柴禾,见妙茹便道:小师傅好啊。妙茹行了一礼,道:老人家好。老樵夫径自走到厨房前,将柴禾放在了檐下,又走到井边,拿起葫芦瓢舀起水喝。妙茹便拿起一盘糕点,送给老樵夫,道:老人家吃些点心吧。老樵夫接过点心,看了又看,对妙茹笑道:这么精致的东西,我这老不死吃了,糟蹋东西,带回去给孙儿吃吧。阿芸见了,急忙道:老人家,你吃吧,还有呢,多送你些。老樵夫看着阿芸,有些犹豫的将一片糕点放入口中,闭着眼睛,嘴抿了又抿,过了片刻,满心欢喜的对阿芸说:小姐啊,这太好吃了,我舍不得吃,让我带回去给孙儿吃吧。阿芸见此,又是无奈,又是心喜。妙茹将那一屉糕点,连着屉笼子都送给了老樵夫,又说,让老樵夫告之附近山里的几户人家,明早来取糕点,庙里有位施主来布施的。老樵夫听了,连忙道好后,捧着那屉点心,回家去了。
夜间,妙茹和师傅在佛堂里诵经,阿芸也跟在身后,盘坐在蒲团上,功课完后,师傅起身对阿芸说道:这位施主,即来本庙清修,就得和我们一道行功课,多吃些苦,也好多修些福。阿芸连忙点头道:我愿吃苦。师傅又对妙茹道:那这几日,你就多为这位施主讲讲佛法吧。妙茹亦行礼答是。师傅离开后,妙茹和阿芸才走出佛堂,本来妙茹给阿芸安排了客房,可阿芸还是求着,要和妙茹同住一屋,妙茹亦无他言。回房后,阿芸从怀中拿出一方手绢,递给妙茹,笑着道:姐姐,看,这才是我给你礼物。妙茹道:这是庵中,不可叫我姐姐,就叫我妙茹吧。又接过手绢,只见手绢上,娟秀的绣着一卷心经,心头一热道:你绣的。阿芸喜道:绣了一个多月呢,姐姐喜欢么?妙茹收下手绢,言道:即是佛经,哪有不喜的道理。又道:早些睡吧,即答应了师傅,明早可真要早起。妙茹解衣卧睡后,听阿芸道:姐姐,我今年冬日就要成亲了。妙茹心头一暖,握住了阿芸的手,说道:和孙璞吧。阿芸道:是的,但我不想成亲,我想和你一样出家,就能日日和你在一起了。妙茹笑道:傻丫头,那孙璞怎么办呢。阿芸道:让他当和尚去。说罢,姐妹彼此一笑。
次日凌晨,窗子还未白时,妙茹醒了,见阿芸还在梦中,不觉一笑,推醒了阿芸道:起来了,行早课了。阿芸迷糊中,喊了声姐姐,随即坐了起身,睡眼惺忪的看了看妙茹,便趴在妙茹身上,嚷着:太早了啊,天都没亮。妙茹见此,忍住笑意道:快穿衣起来,迟了,师傅要责骂的。说罢,挣开阿芸的双臂,起身穿衣,阿芸也随之。到佛堂时,师傅已跪着念起经来,妙茹带着阿芸跪在师傅身后,也随师傅念起经来。辰时初了,妙茹又带着阿芸,来到厨房煮粥,粥熟后,妙茹请师傅食饭,阿芸去竹盒笼里,拿出了几盘糕点,奉到师傅桌前,师傅见此,便道:即是施主的心意,老尼就吃一块吧。妙茹见此,也拿了一块云糕,阿芸倒是只喝粥,心有所期的看着妙茹和师傅吃着糕点,期待着她们多吃点糕点,然妙茹和师傅吃了一块后,不再多食,只是喝粥。妙茹知师傅心意,吃完粥后,将桌上的糕点又放回了盒中。这时,门外传来了一阵脚步声、一阵笑闹声,阿芸跑出一看,原是一群小孩来到庵中,小孩见到阿芸有些羞怯,只是笑着,见到妙茹走出来,才喊着:小师傅,小师傅,我们来取糕点,昨天牛伯说的。原来山中人家,大人们都去山去田做事了,唤自家的孩子来此。妙茹见了,便将阿芸带来的糕点、物件,都分给小孩们,阿芸也在一旁,满心欢喜的帮忙,见有小孩接到糕点后,迫不及待的坐在院中,马上吃了起来,又和伙伴们换着点心,大笑大口的吃着,小小的腮帮子也鼓圆了,还呶呶的说着笑着,阿芸心里也暖着,觉得他们吃了和姐姐吃了一样。孩子们走后,阿芸对妙茹道:姐姐,下次我多给小孩带些来。妙茹一笑道:那是你的功德。
阿芸初时随着妙茹坐禅,觉得双腿僵累,过了几日,习惯了,倒也不觉得累了,庵里的日子也适应了,心里安宁又怡然,比起一人在家呆着,顺心多了,可就在阿芸忘了回家时,接阿芸回家的人来了,七日之期已到。阿芸见到随仆们,便道:谁叫你们这么早就来的,你们回去吧,我再住些日子。领头的家仆看着阿芸,笑也不是,说也不是,就耷拉着头,站在阿芸面前。妙茹便道:说好的七日,就七日,不然把你赶出去。阿芸听了,眉目一蹙一红,喊道:姐姐,家中无人,我不想回去。妙茹心头一凉一温,道:正是家中无人,你才要回去啊。阿芸叹了声气,道:好吧,那姐姐我过段日子再来。阿芸跟师傅告别后,坐上竹舆时,拉着妙茹的手道:姐姐,我是真想也落发出家了。妙茹道:别说傻话了。
春天过去,夏日到了,阿芸还未来,倒有相熟的香客,带着丫鬟,来到庵中修佛消暑小住几日,妙茹心里见此,念到阿芸也快来了吧,有些难自觉的不安。阿芸没来,倒是家中的管家来了,见到妙茹,悲道:小姐,芸小姐病了,想请你回家一趟。妙茹听了,心中一惊,道:病多久了?管家道:一月多日子吧。妙茹便道:怎么此时才告我。管家垂下头去,道:阿芸小姐不让说。妙茹放下手里的经书,去告之师傅,师傅听了,叹息一声道:去吧,人间事莫强求就是。妙茹走后,师傅想起当年,自己请妙茹阿母让姊妹两遁入空门,妙茹之母犹豫三日后,只送了妙茹来庵,将阿芸留在身边,世人的命,总离不开旁人的取舍,亦离不了自心的迷醒,一场大梦后,有什么能剩下,唯佛法慈悲。
阿芸一路上快步而行,问起阿芸的病因,管家言道:城中有名的大夫都请遍了,却也说不出个因由。妙茹心中不免有些焦急,到家后,见阿芸卧在床上,人瘦了许多,脸颊也枯了,心头不免一悲,上去握住阿芸的手道:怎么此时才告诉我。阿芸笑了笑:我总是以为快好了,就没说了。妙茹听了,倒是无言,阿芸又道:姐姐,我觉得我快不行了。妙茹心头一颤,对阿芸道:别说傻话,等身子好了,和我去庵里住段日子,调养一下。阿芸听了,心中一喜,眉梢一笑:好的,早就想来庵里了。这时,大夫来了,妙茹便退身出去,站在门外等着,等了多时,大夫才出来,妙茹便抢上去问询到,大夫看着妙茹言到,医得了病,医不了命,劝家人准备一下,也好冲冲。妙茹心中一片哀沉,头里一阵眩晕,吩咐管家准备后,来到阿芸床前,见阿芸已经睡着了,便握住阿芸的手,阿芸的手好冷,让妙茹想起母亲的手,不觉咽声哭了出来。夜间,阿芸睡着后,妙茹便跪在母亲的佛堂前,为阿芸念着药师咒,望佛祖拔除阿芸的病厄。过了几日,阿芸病情愈恶,有时说起胡话来,有时又把妙茹当成阿母,那日,阿芸病况轻了些,对妙茹道:姐姐,我要走了,昨夜我飘魂了,魂飘在房顶上,看见卧在床上的自己,自己真瘦多了,变丑了。妙茹听了,心如刀绞,安慰着说:别说傻话,那是梦。阿芸一笑道:姐姐,你说人死后真有魂吗?妙茹落下泪来,点头道:有的,好人有好人的魂,坏人有坏人的魂。阿芸也流下泪来,低声道:阿母走了,我也要走了,这一场生啊,真悲哀,可有时又觉得自己还爱着她,放不下。又握住妙茹的手,说道:姐姐,我死后,你回家来吧,替我活下去。妙茹听了,悲痛道:别乱想了,好好休养。阿芸又不甘心的说道:姐姐,替我活下去吧。妙茹心中一悲一苦,含泪道:我既已出家,就要为众生活下去,为阿母,为,为他们。阿芸惨然一笑,又欲说何,然精力不济,阖上了眼目。
夜间,妙茹跪在母亲的佛堂前,对着佛祖画像,在身前摆了一盏灯,将右手的食指,裹上了棉絮,浸了灯油,然后点燃了手指,为阿芸念起药师咒来,焰火灼指,初时觉得痛,痛入心髓,然念到阿芸之死,想到阿芸之生,心念坚定后,倒不觉痛了,心中一片澄明,若雪夜之月,山茶之花。经念完后,妙茹将焦骨掰了下来,把伤口缠上布条,心中正喜悦之时,阿芸的丫鬟却撞进门来,哭道:小姐走了。妙茹闻之,如受雷击,噌的站了起来,注视着眼前的佛祖,哭了起来。
阿芸死后,妙茹留在家中,对亲眷道:自己料理完阿芸的丧事后,就回庵中。亲眷听了,想起阿芸家中的产业,心里倒松了口气,对阿芸也多了几分怜悯,对妙茹多了些同情。妙茹言,阿芸还未出阁,不用大办丧事,就让自己守着她,为妹妹念七日的经。阿芸的棺椁停在院中,点了几盏长明灯,妙茹盘坐棺边,念着往生咒,然有时夜深了,又念起心经来,像是为阿芸念的,又像为自己念的。阿芸落土那日,妙茹言阿芸年轻,不用亲眷相送,就带了几个家仆,抬棺而去,孙璞也来了,与妙茹一道相行。封土后,妙茹让家仆回去了,和孙璞站在阿芸的坟前,良久无言后,妙茹道:看来他们是对的,我和妹妹只有出家了,才能活下去。孙璞悲道:是我命不好,没有和阿芸白头到老的福气。野外的风好大,妙茹似没有听见孙璞所言,只觉那风吹着那盏灯,燃烧自己手指的那盏灯。
过了片刻。
阿芸让我替她活下去,妙茹道。彼此的沉默,世人的多心。阿茹道:但我要为佛祖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