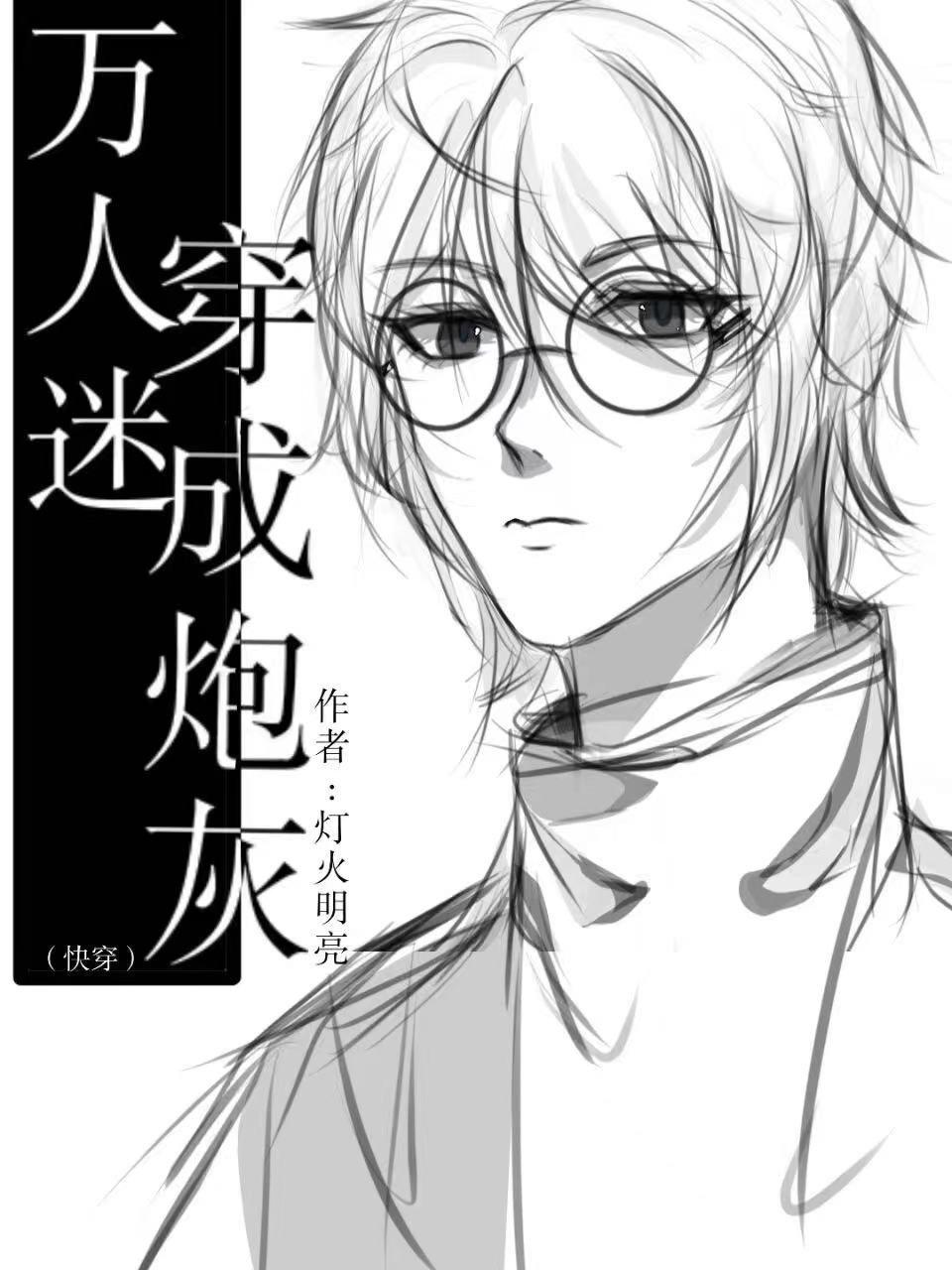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omega上司有尾巴微博作话 > 第89章 第 89 章(第2页)
第89章 第 89 章(第2页)
卢烽感慨道:“是啊,我把你养大,最知道你什么样子,当初把你招进‘雏鸟计划’的时候,才那么大点。”
他比了个高度,说:“十一二岁的娃娃,还不到我胸口,严重营养不良,一张小脸瘦得只剩下一双大眼睛。”
卢上校虽然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可在e组一向说一不二,严厉到不近人情的地步,没有人不怕他,今天却打开了话匣子,像个面对即将离巢幼崽的老者,喋喋不休地忆往昔。
卢烽:“至今我都记得当时那场大火,事出突然,我来不及叫增员或者联系当地的消防部队,听见里边有人呼救,什么也没想,就冲进去了,后来虽然救下了人,可落得我一身残疾。”
那件往事曾经轰动一时,被人口口相传,连平墨这样的晚辈都耳熟能详,像广大“卢烽粉丝”——譬如裴与屠——提起来永远义愤填膺,其实总结起来就是:一位前途无量的特种兵,路见危险拔刀相助,结果因为当时自己并没在执行任务,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受了重伤。
而那位被救的老人,害怕承担卢烽的医疗费,同时又想讹一笔保险,死活不承认是卢烽救了自己,甚至倒打一耙,在媒体上闹得沸沸扬扬,险些害得卢烽受到处分。
好在几经波折找到了当时的监控,才还了卢烽清白,可他却也落下了终身残疾。
身体上的重创,对于一个靠体能的特种兵而言,无疑是毁灭性打击,何况当年卢烽也不过二十三岁。
平墨小时候曾经问过还是e组教官的卢上校,后悔救那老人吗,当时卢烽给小平墨的回答是“保护平民是军人的职责。”
这件事平墨虽然问过,可卢烽还是第一次主动提起,平墨忍不住又问了一遍当年的问题:“上校,您后悔过吗?”
这一回卢烽却避而不答,只摇摇头,答非所问地说“你倒是把我当年的做派学了个十成十”,便换了话题:“还有那一次,派你暗杀一个海盗头子,这只是个普通难度的任务,结果小半年杳无音讯,害得我整日担忧你——别光听我说,喝茶,新水快煮开了。”
平墨乖乖端起茶杯,也附和道:“那一次是真的惊险,还好冷莉救了我,后来她的线人身份和主星合法户口,还是您破格替我批的。”
卢烽长长地叹息:“是啊,好像昨天的事。一转眼,你都这么大了,翅膀硬了,要跟那姓裴的小子结婚也只是通知我一声,从前跟我保证过的话都忘了。”
当初在联军大的内部招待所“交流中心”,平墨曾亲口对卢烽保证“任何一个alpha敢标记我,我都会杀了他。”
往事历历在目,平墨垂着浓密的长睫毛,遮住眼中神色:“您一直待我最好,别的战友都住大通铺,只有我一个人从小就睡单间,这件事连裴与屠都很羡慕……”
那个人为了避免和战友拿错裤衩,还落下了穿花内裤的毛病,直到现在,家里的晾衣杆上还常常一片姹紫嫣红,每每遇见那壮观景象,他都恨不得假装不认识姓裴的。
想到这些,平墨无意识地微微笑起来。
卢烽看着他的目光愈发幽深复杂,平教官随即道:“我真的很喜欢他,您是我最重要的人,我的人生大事,很希望能得到您的祝福。”
“我是你最重要的人。”卢烽低声重复,复又惊天动地地咳嗽起来,平墨习惯性想起身去替他拍背顺气,可刚站起来,便感到一阵头晕目眩,他两眼一黑,软软地倒了下去。
卢烽咳够了,才好整以暇地看着平墨,他比半年前还要苍老得多,脸上沟壑纵横,头发也白了一大半,浑浊的眼瞳贪恋地望着平墨:“既然我是你最重要的人,今天便报答我吧。”
平墨浑身无力,但头脑是清明的,他软软地瘫在花纹繁复的小块地毯上,费力地掀起眼皮:“茶有问题。”
卢烽笑起来,因为喉咙里总是堵着一口痰,所以笑起来也像是一把旧风箱,又引出一串咳嗽。
终于顺了气,卢烽才哑着嗓子说:“还不算笨。”可惜这孩子太信任他,没办法对他提起防备之心。
紧接着,却听平墨口齿清晰地问:“卢上校,遗荒基地的防护网,是你割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