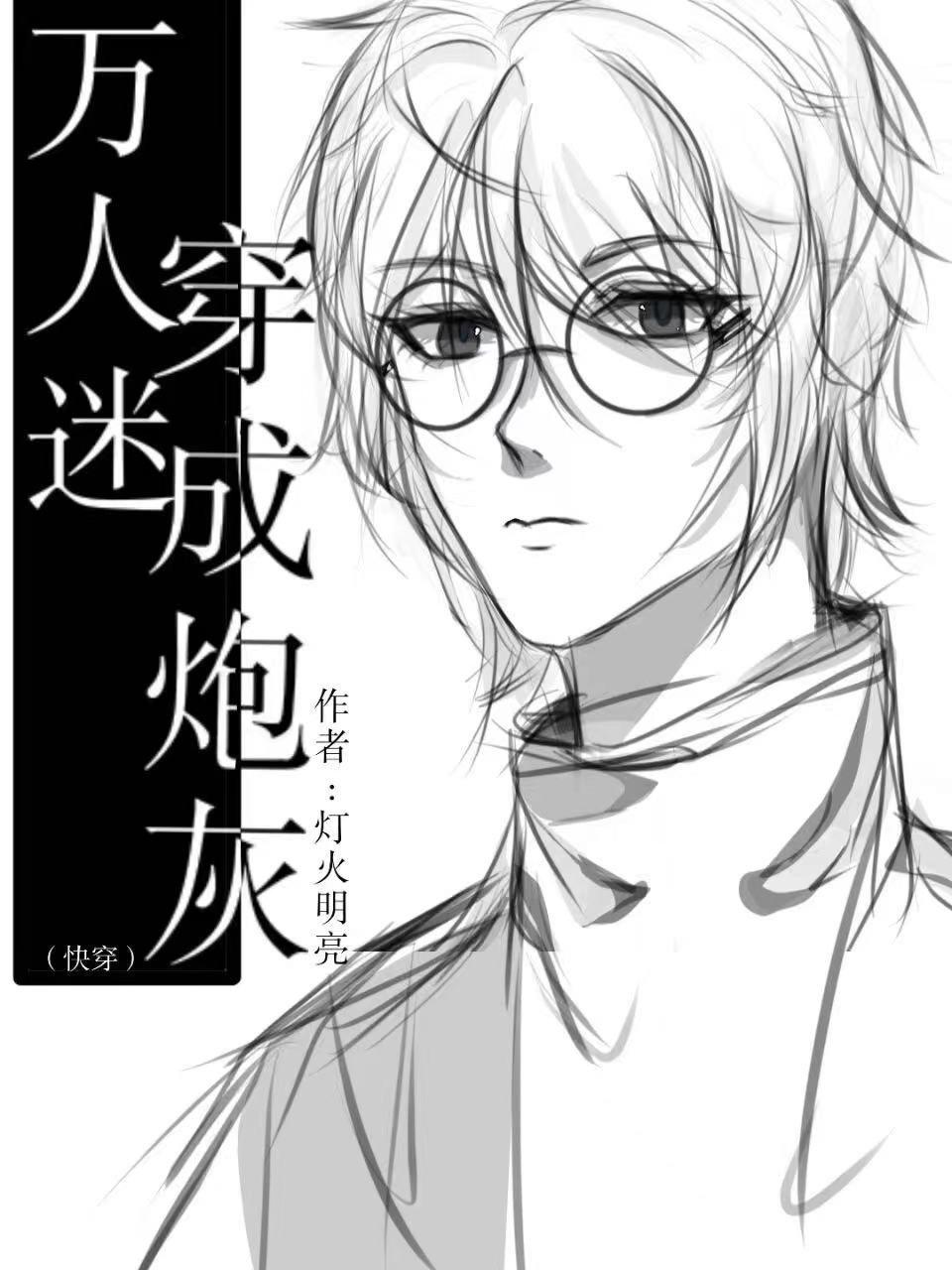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真酒如何成为警视厅之光免费阅读 > 第90章 谁接了谁的锅(第1页)
第90章 谁接了谁的锅(第1页)
松田阵平把围裙潦草的堆在料理台上,从波洛咖啡厅冲了出去,一口气冲到道路旁边,伸手拦下一辆出租。
他人还没坐进后座,就先开口喊道:“去东京警视厅。”
“欸?”这年头怎么还有人打出租去警视厅?这是去报案的吗?前座的司机有些怀疑地回头看了一眼,不看不知道,一看倒吸一口凉气。
坐上车的金发青年一脸凶狠,紫灰色的眼睛里喷射着浓浓的怒火,脖颈和白色衬衣的上半部分还有星星点点的红色污渍,仿佛凌乱溅上去的血点。
司机颤抖着手启动了汽车,用余光瞥了一眼后视镜,只看见后座的金发青年表情愈发凶狠的接通了一个来电,对着电话大声吼道:“。。。。。。杀了你!”
他吓得不小心松了离合,整辆车熄火,车子猛地往前颠了一下,停在原地。
松田皱了皱眉,疑惑的瞥了前座的司机一眼,没有过多理会。
反倒是司机被这轻飘飘的一眼吓得不轻,他倒是想立马报警,可是后座的这位大哥想要去的地方就是警视厅。他该不会是杀了人之后去自首的吧。。。。。。
人过中年、十分惜命的司机先生赶忙启动了汽车,恨不得立刻飞到警视厅去。
后座的松田在刚刚接到了来自某位极度不靠谱的同期打来的电话。
当时他怀着对同期的信任以及配合,心不甘情不愿的勉强把救援新海空的任务让给那家伙,自己装扮成假“安室透”去咖啡厅里端盘子,无时无刻不在等待着来自那家伙的电话,等待着他们的音讯。
一直等待到日薄西山、天色渐暗,也始终没能够等到,在想象中应该慢慢从街角出现、一步步走进咖啡厅的黑发青年。
每多等待一秒,他的内心都在反复受煎熬。他想要打电话过去询问具体情况,又怕干扰到他们的救援,可是他不打电话,另一头始终杳无音讯。
一直到他艰难的挨到距离下班时间还差半小时时候,松田终于忍无可忍的从咖啡厅里冲出来,冲上路边的出租车。
偏偏在这个时候,他接到来自安室透的电话,对方告诉他,人救回来了,但是他不小心忘记通知自己了。这是可以随随便便忘记的事情吗?
松田攥紧手里的电话,一声咒骂破口而出。
电话那一头却忽然换了一个声音。“松田,我没事了。”温和而清冽的声音慢慢响起,堵得人说不出话来。
松田低着头,低低吐槽了一句,“你这家伙——”
“快点回警视厅吧,我和安室先生现在就在警视厅的门口,正打算进去呢。”
“嗯。。。。。。不是啊!”松田刚想应声,猛地想起了什么,低下头看看自己身上一片狼藉的衬衫,有些恼怒的扯了扯被染成金色的头发,“你先把电话给旁边那家伙!”
新海空闻言,顿了一下,似乎猜到了什么,笑着把电话递回给安室透。
安室透诧异的看了他一眼,把电话放到耳朵边上——
巨大的男声差点把他的耳朵震聋。
“你这家伙!快点给我换回来啊!我才不想顶着这一头鸟巢进警视厅!”
安室透后知后觉的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身上的衣服,抬手摸了摸那张涂满易容材料的脸,闷声发笑。
半小时后,两个黑发青年肩并着肩走进了东京警视厅的大门,走在左边那位一头黑色的卷发湿漉漉的垂着,有些僵硬的板着脸。
·
卸掉伪装、染回头发的松田带着新海空回到了搜查课。
原本能够证实新海空杀人嫌疑的证据被逐一推翻,监控录像被重新检查、酒店的安保和工作人员也被迫接受警察的二次排查,死者的人际关系成为警方下一轮破案的重点方向。之后的案件该如何侦破,真正的凶手又究竟是谁,这些都是搜查课需要思考的问题了。
比雪还干净的新海空很快就被无罪释放,可以快乐的回到自己的家里。
他坐上松田的车子,假装很疲惫的靠在副驾驶座上闭目养神。其实这只是为了阻挡松田即将进行的说教。
松田大概也看透了新海空的把戏,皱着眉扫了后者一眼,无所顾忌的打开了车载电台。
车载电台里传来一道激动的女声:“今天下午四时许,我市郊外的一个大型违法制药厂被警方查处,据悉,该制药厂打着制药的名头私自制造、售卖违禁药品。警部,请问你们是如果成功捣毁这一窝点的?”
窝点?
新海空提起几分兴趣,从副驾驶座上坐直了身体,看向车载电台,低声问道:“警方捣毁了什么窝点啊?”
“你不知道吗?”松田把电台的声音调大了一点,目光注视着前面的道路,语气平静的反问道。
他应该知道吗?
新海空皱着眉思索了一会,猛地想起被他弄倒的朗姆开得好像就是制药厂。